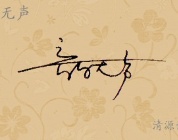天空无色,街景无色。他左下侧的牙齿很疼,疼得轰轰烈烈,疼得空空洞洞。他想不在乎可又不得不很在乎,回忆如一丝极细的琴弦,在风中若有若无的弹奏着,悲戚的情绪哀婉冰冷。
现在他再也不能写作了。处心积虑地涉过人世间的河流,对世事和人性进行过一番徒劳无功的破译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本想等到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以后才动笔这一雄心壮志是何等的荒谬可笑。对的,因为不了解而写作,因为一知半解而停笔,就不用在试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遭遇失败了。也许你永远不能把那些岁月的隐秘写出来,这就是他一再延宕,两眼茫然空洞的缘故。得了,即便是眼前这个精致的女人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就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但愿咱们从来就没有相识过,”女人说。她咬着嘴唇望着他手里举着的酒杯。“也没有相爱过。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就是喜欢听你的胡言乱语,即便在你一个劲地发誓对我说你所说的都是谎言的时候。而且不管哪儿我都愿意跟着你去,而且会很开心。”
“其实清醒的是你,糊涂的是我。”他说。
“这么说是不公平的,”她说。“我一直还是笃信你的,只要你说的我都相信。你不信?只要你吆喝一声,我还会和以前一样撇下一切,不管上哪儿,只要你想去我就去,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真希望你振作一点。”
“你说的是你愿意喜欢的。”
“不,我说的就是你。可现在我有些不确定了,因为你一直在坚持不懈的试图改变我。我不明白我到底干了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
“我想我干的事情就是,我什么也不想干的静静呆着。我什么也做不了,更不可能改变什么。”他望着她,“除此以外,你以为我真的还能做什么呢?”
“你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了,除了说话。”
“嗯。”
“而且只要有对手就呓语连连,无休无止。”
“对。”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那时说你爱我的时候你就很认真,很清醒。”
“记得当时年纪小。”
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
有一会并肩坐在桃树下
不知怎么样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还记得那一晚你说了什么吗?”
“那时我醉了,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什么叫不该说的话?”
“不该说的话就叫做醉后呓语症。”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说过那些话的。”
“那是醉前呓语症。总而言之,我一直就有这个绝症。”
“不,我是爱上了你。你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我现在也爱你。我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男人说。“我不这么想。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别装糊涂,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你现在说的话是有些昏头了。”
“没有,我已经没有头可以发昏了。”
“你别喝酒啦,”她说。“求求你别喝酒啦。我知道你心里有事要做,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陪着你尽力去做。”
“你去干吧,”他说。“我可是已经累啦。”
现在,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那年的他背着背包,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大街的人流中。许多年来,自从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的许多年来,他都一直像这样漫不经心地走在大街上。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此时这般的清醒,他从容不迫地回忆起了心底隐秘的承诺,同时一种极其清醒的冷静,使他察觉到这么多年来,走在如潮的人流里的他,竟然从没有过一种从心灵深处有中渗出的兴奋感和实在感。他停下脚步,对着橱窗里冷漠无言的模特人体上闪闪的冷光,吹响一声华丽的口哨。他很高兴也很沮丧,为现在的心里竟有了这样的感觉。
白白的太阳光像纷纷洒洒的雪花覆盖了这个冰冷的城市,不,那不是雪。这会儿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哩。冰冷的印象其实与雪意无关,与季节无关,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冬天之城。
牙还是很疼,疼痛的滋味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他什么也不想,可牙依然很疼,照样的空空洞洞而轰轰烈烈。
后来,为了转移痛苦的感觉,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胡思乱想,尽量远远地绕开心底渐渐苏醒的隐秘。
深夜里
有一种凄凉的声音
是我在旷野中呼唤着大地
山谷里
有一种不平的回响
是我在内心里无知的觉醒
哦
让我在风里喁喁独行
让我在黑夜里独自哭泣
……
那年,没有掌声,从来没有。这种曾经流行一时的歌曲已经在灯红酒绿的闪耀间褪去了最初动人的颜色。如果不是暂时找不到合适价格的歌手,靖还有机会在这里唱这种歌吗?靖究竟明不明白,全身心地投入深情演绎、微薄低廉的收入,换不来一声轻巧的掌声,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如无其事的品味着杯中的饮料,不动声色。
“唱得不错,靖。”安笑嘻嘻地对着刚从歌台上走下来的靖说。
靖的脸色僵硬。其实靖不会为没有掌声而生气的,他从来都视唱歌为生命,但也从不屑于敷衍的掌声。他一直警惕着一切浮光掠影的东西,他说过他不想因为追求一时间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沉沦于无动于衷的麻木。他心里明白他深情演绎的目的,礼貌的掌声永远和知音无法相比。靖勉强地喝了一口安递过去的饮料,然后直视着那年的他的眼睛,对他说道:“我看见那女孩了,刚才。”
“谁?在哪里?”安满怀兴趣地环顾左右。
靖没有理他,继续盯着我说:“就是她。你知道的,凌说她爱穿一袭的红裙子,趴在墙头上。她在眺望远方,她已经望了很久,也许还要望下去……真的,唱着歌的时候,我就看见她了。”
安不动了,他很惊愕。
他的脊背直发凉,他知道靖实际上在说什么。凌失踪前也说过类似同样的话。靖也要走了,这个麻木狭小的城市,除了随遇而安的安外,连只知道唱歌的靖也留不住了。他有些凄然地想到。
城外的路边有一所古老空寂的大宅院,不知为什么老是有过路的人传言:经常可以看见有一个身着红裙的女孩,一直趴在那堵极高极阴森的墙上向外眺望。她永无止息地望着远方,她究竟在什么,想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凌一度沉迷于这个传言,经常为之陷入冥想,极尽所能地进行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分析和推断,最后就失踪了。
凌不见后,他们曾经去过那个大宅院。它空寂而荒凉。那是一个深秋时分,风吹着桔黄的瓦楞草,阳光十分明朗。推开破败的大门,里面有一个潮湿、荒芜的庭院,空寂无人,墙角堆着瓦砾,那里有个断裂的石凳,一口也许干枯了的井。就没有一丝人住过的痕迹。但他们明白,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女孩把凌带上了去远方的路。
靖还在很认真地看着他,他有些惶惑,不知如何说话。最后他挣扎着勉强问道:“你看见啦?”
“我看见了,很清楚。”
“你还唱吗?我有点累。”
“走吧。心乱哄哄的。”靖走向歌台,和那个头发老长的电贝司手低声说了几句,提起吉他走下来,向门外走去,安紧跟了上去。
他们走了,他却又坐了下来。歌声又起,一个平淡无味的歌手扭动着登上了歌台。
后来,那年的雪孤独的下了整整一个季节。
关于这些,他一个字都没有写进自己那本估计销量将会很好的书里。
还有一年,他在路上。曾经一度为了搜集整理一首濒临失传上古歌谣,他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整整一个冬季没有离开山林一步。当鸽哨声清越的划过冬季的晴空,他推开木屋暗淡蒙尘的窗户,骤然发现弯弯的山道边的一株野樱花树,已在一夜之间摇曳怒放。一个小女孩捧着一束刚采下来的樱花,哼着歌走过,脸上绽放着花一般醉红的快乐。

 我们曾经失去控制
我们曾经失去控制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