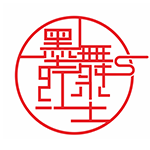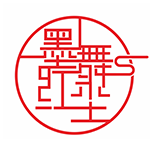“繁华”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
在码头还没绝的时候,那条街的繁华无可比拟。街里的老人说,河岸边是一长绺摆。摆是什么?拴船的铁环子。系船时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那时候上上下下,走水路的,走陆路的,都要到这条街歇口气。吃一袋烟,喝一碗茶,有时还闷一盏子酒,侃几句大山。遇到饭点,坐在油腻腻的八仙桌边,大口吃肉。吃完,袖子一抹,衣服全是牙齿浸润过的油迹,像阳光从树叶间滤过下的光斑。然后浩浩荡荡神神气气离开。本地人把这叫“歇脚”,或者说“歇肩”,用现在的话就是“闪一口气”。那个时候,街两边的冷饭铺密密麻麻,从早到晚老是船老大的嘈杂声……
这样的时光据说有好多年。
街里的老人还说,怪要怪那几个不安分的读书人,以为治国是在书斋里念几句“之乎者也”,硬是要搞什么变法,变成天下大乱,连河道也不安分。我起先对老人的遗言如云里雾头,后来有幸读到这条街的街志:光绪24年,西元1898年,从农历六月十五到二十九,天像破了一个洞,大雨不歇气地使劲从洞里掉,洪魔泛滥,沿街的河堤像汉高祖刘邦刀下的那条白蛇,斩成了数截,咕咕冒出的血气吞没了人们的哭声。洪水退后,满目疮痍,几个主事的人商量重新筑一道堤,让河水挪一个窝。奇怪的是这主意一定,就天下太平。那几个不安分的读书人也像洪水一样,蒸发的蒸发,逃窜的逃窜。1898年是农历狗年,历史上把这几个读书人的折腾叫“戊戌变法”,也说成“百日维新”。这个狗年注定犬吠声四起,包括这条河的不安分。但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不安分的读书人中一个叫康有为者,后世有人还称他“康圣人”。
街里讲这种话的老人我从来没见过。按照年龄推算,我的老父亲也没有见过。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一百年之于宇宙,是鸡眨眼的工夫;之于一条街,风里雨里虽然难熬,其实也一样。因为那些最初关于街的记忆者,在鸡眨眼的工夫中,也没了。失去了记忆,谁还会感到疼痛?但关于街的繁华,用我父亲的话说,从此水落三秋。将一条街的蜕变与水落三秋关联起来,是父亲说过的最深奥的话。几十年来,我还没有勘破。
自经历1898年的那场洪灾以后,这条街与河道彻底分道扬镳,像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心存芥蒂,各奔东西。河道离开街后,河水变得越来越浅,终至于有一天无法撑船,船工们作鸟兽散。街,也开始衰落,渐渐的只成为附近村民的一个集市,恢复了“街”的本来面目。再后来,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氤氲,让“推进涌出”变得格外稀奇,除非每年腊月底的那几天。
最早关于街的传说,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亭集又叫“郑家集”,历史还算悠久。当年李世民夺天下在此遇险,被一郑姓大户所救,登位后御赐“郑家集”,其郑姓子弟多有封赏。郑族世世代代经营此地,建有四门城墙,高阁崇楼无数,甚是风光。后来,郑家出了不肖子孙,吃喝嫖赌将一干祖业尽数卖给王家和刘家,王、刘本是互相通婚,就以官府名义把“郑家集”改名为“王刘集”。到了元末,据说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时在此要饭,被刘姓一管家奚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有恩报恩,有怨报怨,就将刘氏一族充军岭南,其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刘氏有脱逃后生心怀不满,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一把火将刘氏旧居化为灰烬,后来就没再修复。县志记载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邑民死伤无数。朱元璋听到此消息后,就将充军岭南的刘氏后裔全部活埋,让刘氏灭族。此后,“王刘集”干脆就恢复“亭集”名。现在,经过几百年风雨洗礼,亭集只有一条窄窄的街道,供人们早集……我这文章是一篇小说,文中的“亭集”就是按照这街的传说记述的。如果不是那一把火,假若四门城墙还在,1898年移河改道前的繁华,就小巫见大巫了。那街道也不会孤零零一条通到头。有些事一失足还不只是千古恨。
当我与这条街交集的时候,其时,它还是只有一条主干道。东北西南向,头对头四五百米,清一色瓦房,门朝街道。门是木板门,一块连一块,像竖着的仓板,早晨一块一块卸开,天黑又一块一块拼上。七十年代后期,那些国营单位:百货公司、副食品店、书店就将这一块一块的木板砸烂当柴烧,各具特色镶上大门,有木质的,也有铁门,后来还流行卷闸门。集是早集,天没亮,人就涌了过来。卖米的,粜麸子糠的,卖茅柴、要子、草鞋的,集中在街的南头;卖时令小菜,鸡蛋、猪仔、筛子、箢篼、筲箕的就在北头。不是约定俗成,而是习惯。这些占道经营,将街心让出一条道。在南边的街集上,有几个管理卖柴卖米的,手里拿着一杆秤,秤一称,收一毛两毛过秤费,特别神气。集市两边的铺子都是公家的,连剃头铺也属村集体。食品公司是街上最好的单位,老百姓偶尔割半斤一斤肉,除了要肉票外,还要鸡不叫就去站队,稍微晚一点就可能放空。所以,那年头食品的人最吃香,平常人家割一点肉全凭运气。一般百姓如果跟食品有点关系话,那绝对值得在人前炫耀。这不是街的错。其时祖国大地都一样。计划经济,什么都要计划,这就是特色。街上有一所中学,还有一家医院,大门都对着街开。在电力匮乏时,学校、医院柴油机发电的突突声,成为最明亮的地方,让有学校有医院的街在夜晚并不太寂寞。那时,街是人们的中心,政治中心,柴米油盐中心,读书、唱革命戏和出生、病死中心。
我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好时代的标志是读书不再无用,而且读书还可以改变命运。但我读书不在那条街上,那时没有择校读书的可能和必要。我所生活的地方,距街七八里之遥。在初中之前,每上一次街都很郑重,头天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大人们叫“赶集”。在街市的嘈杂声中吸引人的还是油条摊,开炸的油香在空气中弥漫,像一叠叠云在眼前翻滚,搅得馋神经不知如何吞咽。如果大人开恩,能吃上一根油条,那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我相信很多从物质匮乏年代走过来的都有这种感觉。无论什么年龄段。上初中以后,在校住读,大人觉得在村里剃头交年费不划算,每隔三两个月会上一次街,在剃头铺,剃头师傅一阵滥砍,头发像乌丝纷纷落下,轻松极了。
很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个白昼。
八月天,大地干得冒烟。凭着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条,父亲弓着腰,拉着一板车谷,向街上的粮店奔去。谷袋是洗干净的碳胺和尿素袋。碳胺袋粗糙,纹路稀。尿素袋致密,里面还镶有一层,软软的。那个时候已经分田到户。这些袋子,都是下田地肥时小心翼翼留存的,如果碰巧哪里有个缺口,母亲就会在午休时,坐在门槛边用废布缝补好。那一车谷需要三百六十斤。三百六十斤能够改变一个农家子弟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是划算的。那个白昼,路上的炎热,脚像瓦片在火上烙。父亲弓着腰在前面使劲拉,遇到上坡我在后面使劲推,完全没有感到脚板上的烫。因为正是交公粮时节,卖粮的人格外多,在离粮店大门百多米的大街上,浩浩荡荡都是卖粮的队伍。烈日下暴晒,人们浑然不当回事。相互说着不咸不淡的话,至多拿一条透着汗味的毛巾擦脸。每隔十几二十分钟,板车可以挪动一车长的距离,直到太阳快落土时父子二人才饥肠辘辘转身。整个白昼,虽然商铺不时飘出香味,硬是没想到要买一点垫肚子的硬朗货,渴了就随便在粮店喝点冷水。这是与街道亲密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那时候为了命运改变,做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我渐渐明白,不是所有命运的改变都是好事。当然,也不是所有命运的改变一定是坏事。曾经以为,对于这条街道来说,自从我交了360斤的农转非口粮后,就会像一只鸟,离开这一方天地杳杳无踪。不曾预料的是,几年后从这里转走粮油关系的我,又凭着一张纸,将粮油关系转回来。那时,我是街上医院最年轻的医生,会计工资表册顺序号第36。

 对一条街的追忆
对一条街的追忆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