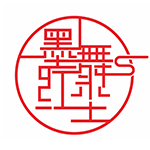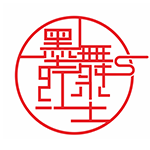老屋的墙,仍稳稳地站立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将故园守望。在日晒风吹雨淋的沧桑岁月中,依旧挺立着旧日的坚强。
自从三哥买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平房并入住后,不觉已近十年光景。搬进新屋后的第三年,三哥因要在新屋前再盖几间小屋,才将老屋上的瓦和檩子拆下来用了。于是,老屋从那时起,就只留下高高的墙了。每次回家,我都少不了要去老屋看一看,看她命运的痕迹依稀,看她情感的春秋依旧,看她厚实的存在依然。老屋,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屹立不倒!
老屋之所以在我的心中有如此的重量,是因为老屋承载着我们家一段长长的历史。她在风霜雪雨之中见证了家人的勤劳坚韧,见证了家庭的和睦团结。老屋经历了三次变迁,每一次变迁,她都将物质的贫瘠升华成精神的富足。
第一次是祖父、祖母带着伯父、父亲、叔父、大姑、老姑从老堂屋即祖居的大家族中分家后迁至老屋如今所在的位置。那时老屋以土坯作墙、顶上覆之以茅。虽然简陋,但在彼时能盖得起房子的人家寥寥无几。解放前,祖父靠做布匹生意及贩驴马的买卖,以勤劳与智慧挣下了一片家业,在当时也算是远近悉知的殷实人家了。正是这个原故,却招来了一帮土匪的觊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那帮匪徒荷枪实弹而来,祖父奋勇抵抗,以立柜与桌椅在屋内顶住家门,匪徒们力冲不进,于是开枪了。匪首连放数枪,子弹穿门而入,击中祖父左臂肘部,当场血流不止,匪徒们这才得以闯入屋内,并欲对祖父下毒手,在祖母带着全家人的苦苦哀求之下,才得以保住性命,祖父从此落下终身残废。匪徒们将屋内所存的布匹及驴马悉数打劫了去,顺带将钱财及家当洗劫一空,自此祖父家一蹶不振,一下子跌入穷困潦倒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过了些年月,又赶上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祖母与叔父相继故去。那时父亲也不过十七八岁,过了两年,母亲加入了这个家庭。一家人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整日处在朝不保夕的边缘。虽然稍后的年月在祖父的带领下,家庭稍有起色,但仍是不济。殷实之家变成贫困之户,老屋作了历史性的见证。
岁月流转,又是几年光景,伯父分家迁出,两个姑姑也相继出嫁。老屋里剩下祖父、父亲、母亲和四岁的大哥及二岁的二哥。再后来,三哥与四哥也挨肩出生了。几年之后,我来到了人间,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家人住在老屋里,虽然生活仍较贫寒,却很和睦融洽。
那是处于大集体的年月,父亲为了养活一大家人,申请与大队里的另几人做起了养鸭的副业。再后来,两个妹妹相继出生,母亲带着我们七兄妹在家。经过父母几年的辛劳,家况似乎有所好转。这时老屋也破旧不堪,风雨侵蚀着墙垣,屋顶上的茅草渐见朽烂。晴天倒好,犹能从屋漏中看到太阳的光线照入,连成柱状的光圈;但若逢雨天,那可就糟了,可谓是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了,这使我想起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描写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句子来。而每次下雨,我就用那只脱瓷的洗脸盆在漏雨处接着,听着雨点打在盆中的声音,真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
终于有一年,我已无法记清具体年份了,老屋开始了第二次变迁。因为父亲做副业的缘故,家里稍有些节余,又从亲友处借得些钱粮,决定盖新房子了。这次的新房子,仍同祖父盖房时的形制,是起尖的立房,只不过将土坯换作了“犁扎”,将茅草换作了陶瓦。茅草房变成了瓦房了。
且说做“犁扎”,这可是一项极为辛苦的活计,而且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秋收后,立即选一块稻田,将积水排尽,再把稻茬子悉数铲平,根却留在泥土里(事后我才知道其根系之交错有补强之功用,类似如建筑材料中加入纤维的作用)。让太阳晒上几天,赶了牛,架上石滚,在稻田里纵横地来回碾轧起来;之后又晒上一两天工夫,再碾轧数遍;复又晒上一两天,要进行第三次碾轧了,这次碾轧作业,须在边碾轧时边薄薄地泼上一层水,同样是碾轧好多遍。就这样,田里的泥已被彻底压实,且板结成块,这样让它过一个晚上。次日晨,拿了一条长长的绳子,由四哥和我在碾压面上拉直线,先拉纵向的线,大哥、二哥和三哥轮流沿那线用脚踩着踩锨,踩锨的形状类似于倒立的“丁”字,作业时将锨背直踩到与碾轧面平,这踩下的深度就等同于“犁扎”的厚度了。踩一锨拔出来,接着再踩一锨再拔出来,如是反复一锨一锨地踩将过去,将那板结的泥块切出一条线来,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如法炮制,再拉横向的线,再沿线切开去。如此一来,纵横的线一交错,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长方形,这长方形的尺寸是由父亲现场示范并规定好的。在踩那踩锨的过程中,有时四哥也去踩上一阵子,但是踩不了多久,我有时逞能也去试一下,哪里踩得动?这种工作,要三天才能完成。等全部踩完了,哥哥们的脚是又疼又肿了。接下来就是取出那长方形的板结块了,这下要用到另一种工具——传锨。传锨的形状较奇特,有点像“工”字形,锨板与柄几近平行,中间的连接部分是锨板延伸出来的,垂直向上有一个接口,接口内安装了一根长柄,柄与接口相交处设置了一条较为粗长的绳子,绳子上系有一根横木杠子。起“犁扎”时,一个人在后面手握长柄,两个人在前面对称地握住横木杠子的两端,以后退的方式拉动,三个人是面对面作业的,传锨受力向前移动,刚好到达事先已被踩锨踩好的长方形的长度,这时握柄的人将这一块托起侧放于边上预留的空位处,这一块被起的长方体,就是一块完整的“犁扎”了。握柄的人往往是父亲和母亲,有时大哥也上手操作,拉木杠的人是二哥和三哥,有时四哥也能替一下,我只能偶尔打点下手,主要是防止“犁扎”倒下去。两个妹妹尚小,只能隔不久送一暖壶水来给大家喝了,祖父因上了年纪,单留在家里看门和烧水。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两天就将足足二斗田的“犁扎”起完了。然后让它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在我的记忆中,一家人同时在一起劳动的场面,就数这一次最为深刻。
传锨和踩锨是专门用于制作“犁扎”的工具,自家是没有的,还是母亲从舅父家所在的村子里借来的。得赶着劲在两三天的时间内做完,以方便别的人家借用。“犁扎”做完了,盖房子的工程基本上完成了五分之二。
因事先已做好筹划,当“犁扎”晒在田里的那段时间,亲友们来帮手扒去旧房子,清理房基地,接着放线、起基槽、下基脚,这些工作接近完成时,我们几兄弟开始让牛套上架子车,将“犁扎”一车一车地拉回,垛在院子里。这时刚好赶上砌墙了。亲友中本来就有在土木业上在行的师傅,又因家里帮手多,几天就将“犁扎”全部垒作高墙了,于是择吉日上梁。上梁当日吉时到,将五千头的大鞭放起,引得村人围观,那日少不了做一顿好饭菜款待亲友们,一派喜庆气氛。当日下午在屋梁上排好竹竿,并用钉子钉牢,次日即开始铺瓦,一日即完成。最后一天以泥巴浆子将墙体的内外糊上厚厚一层,将屋内的杂物清理干净,新房子就彻底完工了。终于有新房子住了,一家人甭提有多高兴了。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大哥、二哥和四哥相继结婚,他们都是在老屋举办的婚礼,又都是在结婚一年多后分家,并先后住进自己盖的新房子。老屋里仍有祖父、父亲、母亲、三哥、我和两个妹妹住着。一九九二祖父去世,从老屋中移就鹤驾,一九九三年父亲因病去世,亦是从老屋中往赴灵山,家门接连不幸,老屋不改朴实与厚道,一如亲人之不离不弃。一九九四年,母亲不愿让本就是大龄的三哥的婚期再有延缓,决定将三哥的婚事办了,婚礼依旧是在老屋中举行的,母亲说这是给家里冲喜,同时也是给老屋冲喜。
再下来的几年内,老屋又迎来了一连串的喜事,先是大妹出嫁,两年后小妹出嫁。三哥也得弄瓦之喜。在我结婚前,三哥已搬出老屋住进新房子,老屋如完成了她的使命。我的婚礼未在老屋举办,那是因为一则妻子娘家距老屋较远,一则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进了城里,在城里结婚并定居了。这大概是老屋对我的祝愿吧。

 老屋
老屋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