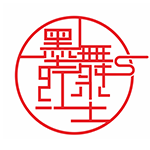我说,《三梦记》实是一写友情,二写亲情,三写爱情,有那么一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意思在。不说它了,咱们喝酒,举杯。
桌面上的牌摊开来打,朋友邀起,酒劲上来,便无所不言,说开了,我便将自己的梦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了。作为一介平民,我没有类似阿里巴巴的大富之梦,也没有大风起兮或大鹏展翅的超脱之梦,更没有青云直上、信步龙庭的宏图之梦,我的梦一点也不高大上。然而我的梦时间跨度很大,任此心挥远行阔,在梦的疆域纵马由缰,牵一根神龙不见首尾的线,把岁月串起来,演成一道道新剧。
3
很小起,我就怕看天空,特别是朝霞和晚霞,通红如血,令我心惊肉跳,恐惧到了极点。我无数次地梦过满天的血红,象一件均匀地渗透着鲜血的血衣,那血是流不动的,板结的,完全凝固在我的视觉和感觉中。血天里,无数的大飞机,就是能丢炸弹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一片,密密麻麻地来袭,如同攫取生命的鸷鸟,猛烈而阴险地扑过来。那时很懵懂,只知道害怕,也不知道究竟怕什么,就大哭起来。大人们听到小孩子在睡梦里梦,也不知道究竟哭什么,只是摸一摸我的额头,算是压了惊了。和平日久了,才知道怕的是战争。无数个黄昏,黑夜,凌晨,同一个梦,都在枕边萦绕不去。
年纪大了,倒是很久没做过类似的梦。有晚,居然又进到那个梦里头,梦到我时,已经躲到一座葱郁的森林里,一架飞机俯冲下来,扔下一个炸弹,轰隆一声将我炸醒了。此后再也没到这个梦境里去过。
梦是不用听的,只能看,于是在梦里我就是眼睛,一双眼睛。我是梦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我曾多次梦到过一场大火,点点滴滴地回忆起来,仍然仿佛身临其境。
那是一座码头,石级高耸,从山边一直延伸到水边。两边是高高低低的木屋,店铺林立,有人在里面打理着生意,迎送着来人去客。荷担提筐者,空手来去的人很多,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都在用一种我从来就不熟悉的乡音打着招呼。水边也有吊脚楼似的房子,一字排开,有点象凤凰古镇的样子。码头外的河滩上,静静地躺着不少的乌篷船和挂着白帆的大木船。总之,那里有相持不下的热闹与安静。
正当我留连在这诡谲的场景里,毫无方向感的时候,突然就起火了,那火势篷然从某个角落起来,然后燃向所有的木屋,食髓知味一般舔舐着,吞噬着,燎然的烈焰呼地腾空而起,象一柄巨大的火把,将天空也烧成了火的颜色。
大火基本上从梦的开头烧到了梦的末尾,梦里的火张牙舞爪地吞掉了那些实体的东西,包括活在梦里的人。待我看清楚时,那些木屋早成了焦炭,冒着冷烟。我惆怅地伫在梦中,没有看到一个人从火中逃出,没有看到一个。
这是一场使人难以顿悟的大火。我知道,过去长沙也曾起过大火,但梦中的火显然与长沙无关。后来,我看到一张火灾的历史照片,方猛然惊觉,解放前夕,重庆朝天门码头的大火,劫后惨境恰和我梦里最后定格的镜头一模一样。
十多岁起,总是梦到一所房子,灯光黄黄的,三五个工人在里面装修。我是那所房子当然的主人,去的目的应该是监工吧。但我似乎并不急于落成,只是看一看,便梦回了。每去一回,装修便有些进展,地板贴了,柜子开始做起来,后来连顶也开始吊了。这个梦,我做了好几年,就是几年当中,总会回到这个梦境。直到有一回去,对着工人们发了一通脾气,说装修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完成啊。后来心内一想,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马马虎虎弄完就算了吧。自此也不再去监工了,此梦宣告结束。十多年之后,自己买了一处房子,请了工人装修,一日去看时,梦中的情形与现实的情形竟然重叠了。
一夜忽梦远山如黛,苍翠如璧,缜密的阳光中,细润的朝露被晕染着泛出湿漉漉的异彩。大片青山下,青砖碧瓦,村屋连绵,人烟繁茂,主街上热闹非凡,赶集摆摊的释放着山货和水货,卖凉粉的、卖面皮的、卖玩具的、卖水果的,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烧烤和炒烩零食的人挥带起蒸腾的香味四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戏台上古装粉黛出演的角儿,漪婉动人地唱着,戏台下看戏的人卖力地叫着好。我独自在街道上游荡,在拥挤的人群中钻过,看着那些欢笑着的人们,自己形单影只,默然抬头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忽地洪水不知从哪个方向蓦然涌来,滔天敝日,排山倒海地一推而过,浑浊的大水转瞬便淹没了村庄,将那些热闹的街景席卷而去,把我看到的美好冲刷得一干二净。我拔脚便跑,跑得象飞一般,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顶峰处方停脚喘息,举目看时,只见山下一片汪洋泽国,生灵皆成鱼鳖……
难道我的身世与某个乡村有关?我的前途与某个乡村紧系?但众人皆没我独存,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时想得头痛,不知甚解。
不久我失业了。
失业前的梦让我心绪难安,失业后的梦则更加怪异。
一夕梦一秀士着白衣长衫,背手而立,嘱吾道:
亭台楼阁下神仙,
白云深处岂无烟。
三十六载成虚幻,
朝来暮往好耕田。
声音沉雄却又充满坚韧和力量。待要追随这个声音时,却发现那人已经不见,只留下一剪飘然而去的白色背影。他脚步生烟,如腾云驾雾,踏歌而行,放歌而去,那歌声飘渺,蓦地耳熟能详,似在前尘里听过千百回。此时掠过耳边,温慰浮生。
醒来时正四更天色,东方未明而歌声似犹在耳,而那首诗偈,我一个字不拉地记下了。后来与一之老师讲述这一过程,她惊讶道,这是一首合乎韵律的诗呀。可那时候,我没接触过诗词韵律,也写不出这样的原创来。我只是按照梦境记下而已。
三十六岁那年,也是机缘巧合,涛哥顺手安排了一批人走上工作岗位,其中便有我。第二年,涛哥来长沙,考察社保和劳动再就业部门,我正在民政局,与柳局长一道,从迎宾路追到八一路,又从八一路至沿江大道,终于还是没能握上涛哥的手。当年,长沙果然评为了全国社保和劳动再就业的先进城市。
涛哥是神仙吗?是的,在我的心中,他就是天上的神仙一样。我暗含感激,伏案耕耘至今,不觉已近二十年了。
4
我从来没有梦过她。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触动那个梦她的机关罢了。
有一晚,我却真真切切地与她在梦里重逢。只有圣洁之心,绝无亵渎之意。
一轮硕大如盆的白月光中,天幕下兀自落下雨来,但,仅只一滴雨。不,那只是一滴穿过时空的泪水,曾挂在三秋的枝头,偶尔刺破了连绵的光阴,落在我的手心。心心念念的就这一滴,长醉复醒的就这一滴,红尘人世只这一滴,已够了。一滴雨泪中,隐去的满天风霜,兀自在尘寰动荡难止。美人的脸,绝不会是如盆的月,幻化成她脸庞的,必定是那滴梨花带雨的泪了。晒在月光下的美人眉清目秀,带着清澈的慈悲,用她善良、忧伤、怜悯的目光照亮了我。
一首歌唱道,一生中最爱的人啊,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这是我唯一一次在梦中把她的样子看清楚啊。
我反躬自问,我爱她吗?既然爱,又为何错失?
回想前事,白首同心梦难圆,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王洛宾在给三毛的诗里写道: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且莫对我责怪……
我知道,人这一生,总要离别的,生离,或死别,其实完全没有不同。好梦不必强留,好人自存于心。无论天涯海角,她健康,幸福,就好了。
说到三毛,她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令无数人动容。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难归。三毛对生命的看法与常人不同,她相信生命有肉体和死后有灵魂两种形式。梦,便是灵魂背着愿望在奔跑。贾大师评三毛说,如果生命是一朵云,那它就是一朵云,如果生命是一阵风,那它就是一阵风。它的形制,它的嬗变,它的流离,都是自在的。

 华胥谁寄锦书来
华胥谁寄锦书来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