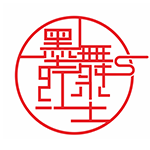宅在家的这几日,读书、做饭与赏花起了大安慰。
腊月二十九的那一天,我去楼下花店买了几束鲜花。在客厅放了一大束百合,书房是几枝风信子,卧室的床头柜放了两枝腊梅。那一天,它们还是含苞待放。这几日,该开的都开了,没开的也快开了。
许是阳光太好,又或者温度升高,花香满了三室一厅。起初感觉略有过,近来都快察觉不到了。果真是久处芝兰之室而不觉其香。今天,我整理房间,观察了它们一会儿,发现大部分百合都开得绚烂,有三枚百合蓓蕾仍在酣睡,白色的苞衬着碧油的叶,姿态安详静谧,竟有几分少女的韵味。风信子有些累累垂垂,倒是那腊梅开出了禅意,配着古朴漆黑的陶土小圆瓶,枝条枯瘦错落,黄花娇柔幽艳,明明是冷冷淡淡的组合,却流露出若有若无的妖娆。
这……许就是中国式禅意美学的妙处:看似极力清净六根,实际最恋奇香异艳。一个不忍,就在电光石火之间显露欲望。所以得收着,如那些粉妆玉琢的层层花苞,极力半开半掩,生怕被人看穿。
我,始终欣赏不来这种造作。还是推崇爽快一点的路子。许是这十二年来,被西方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的浸淫日久,不信“宿命论”,不吃“什么劫什么难”那一套。疫情发生之后,朋友圈们都在对“吃野味”的现象口诛笔伐,我不置一词。咋说呢?我也不吃野味。我不吃是因为觉得它们不好吃,却从未想过环保与安全。
犹记得二十年前,我吃过野猪肉。口感如何早已忘记,唯有那个腥臊气儿与难嚼劲儿,隐约还有记忆;十年前,我吃过清炖喜鹊。那是朋友在山上打猎打到的,清洗好之后送来给我,我交给母亲,母亲用高压锅炖了一个上午,我吃到嘴里除了柴与硬,连个荤味都没啃出来;还有什么野兔肉、鹿肉、斑鸠肉,都忘记是在谁家餐桌上品尝过的了。至于果子狸,我是没机会碰的。一是小时候也没条件沾到这东西,二是非典时期它是背锅侠,我在大学里被圈禁几个月全拜它所赐。走上社会,偶跟人闲聊,听谁提到它的美味,也是嘻嘻一笑,从来不接这个话题。到了今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高发,蝙蝠成了病毒源头,顺便洗白了03年的果子狸,我还是不以为然。
我不以为然实在是……牛羊猪肉和鸡鸭鱼肉够吃了,论齿舌之间的脂厚油流,自然是越肥烂越动人的蒸羊肉、炖牛肉、卤猪蹄、烤乳猪并列为魁;论口腔里边的回味无穷,自然是九宫格的火锅、五香味的烧鸡、皮脆肉酥的烤鸭、鲜美嫩滑的鲈鱼值得称赞。况且,我始终认为,肉食之美的重点不在于肉质而在于烹饪。烹饪的重点又在于火候与调味。只要烹饪功夫深,豆腐都能做得仿佛绣花针。
我国还真有一道菜能把豆腐做得仿佛绣花针的。那就是“文思豆腐”。传说,这道菜是乾隆年间一个叫文思的和尚做的。他虽然是出家人,却是练得一手好厨艺。尤得称赞的是他还有一手好刀工。他能把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在弹指间先切成超薄的片,再切成绣花针一般粗细的丝。他把豆腐丝放入煮开的汤里,那些被汤水润开的豆腐白丝逐渐如云霞般弥漫,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这本事着实难得,被清朝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里记载道:“文思字熙甫,工诗,又善为豆腐羹、甜浆粥。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思豆腐。”
令人打趣的是,文思豆腐本为和尚做的素菜,却需要鸡脯肉与熟火腿、竹笋、香蕈、胡萝卜切丝作陪,还需要用吊出的老母鸡清汤合淀粉勾芡打底。讲究到这般程度,哪里是青灯古佛的出家人用以饱腹的斋饭?简直能登上皇帝的饭桌了。别说,这道菜真就被皇帝享用过。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期间,就青睐上了文思豆腐,将它列为淮扬名菜。从此,这道菜身价倍增,一直流传至今。
可见,好吃的食物不见得非要多稀罕。无奈世人总是认为“物以稀为贵”,吃一些别人吃不到或者吃不起的野味就好像捡了别人都没赶上的大便宜似的。这种劣根性不止现代人有,古人也有。比如谁?苏东坡!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个吃货。他爱吃不说,还爱嘚瑟。
无论他嘴里吃到个啥,都非要写首诗或者写封信嘚瑟嘚瑟。比如他发明的那个“东坡肉”,跟现在的红艳香郁的红烧肉完全是两回事。苏东坡整出来的那个肉啊……就是白水蒸猪肉,又或者该叫白水蒸猪头。详情请见苏东坡的《蒸猪头颂》:“净洗锅,浅着水,深压柴头莫教起。黄豕贱如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有时自家打一碗,自饱自知君莫管。”试想,没有用八角茴香,也没有料酒冰糖,就把一个白花花的猪头搁在笼屉里蒸,出锅之后再配点盐和酱油,吃到嘴里是啥滋味?
也许有人会质疑:你咋知道苏东坡蒸的猪头除了放盐和酱油就没别的调味剂?
还真是。八角茴香在宋朝是被人们普遍作为香料的。除非处理野味或者做汤,极少在烧菜时使用。南宋周去非所写的《岭外代答》有云:“八角茴香,出左右江蛮峒中,质类翘,尖角八出,不类茴香,而气味酷似,但辛烈,只可合汤,不可入药,中州士大夫以为荐酒,咀嚼少许,甚是芳香”。至于冰糖,宋朝的王灼到了1130年才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专门研究怎么通过种植甘蔗制糖的。而且在当时,甘蔗只在福唐(位于福建)、四明(浙江)、番禺(广东)以及广汉、遂宁(四川)地区种植,制糖的民间作坊也数量有限。非富即贵的家庭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糖霜”这个东西。
加上北宋人民爱吃羊肉,其次是鱼肉。他们普遍认为猪是低贱之物。富人不屑吃,穷人不懂怎么吃。苏东坡倒是琢磨出来个法子,即小火慢烧罢了。一直到了明朝,兰陵笑笑生才在《金瓶梅》里托宋惠莲给“蒸猪头”加了料:“起到大厨灶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论蒸猪头的时间,算下来也得俩钟头。
苏东坡吃个蒸猪头嘚瑟不算完,他吃个果子狸更要嘚瑟。严格来说,后人们掀起吃果子狸之风,离不开苏东坡的“安利”。
想当年,好不容易从“乌台诗案”里脱身的苏东坡,接到朝堂指令下放黄州。可能是牢狱之灾刺激了他的心灵,虐待了他的肠胃,他从此对饮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东坡在黄冈大快朵颐,什么武昌鱼,什么深山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什么烧野鸡(烹煎杂鸡鹜,爪距漫槎牙),什么鲫鱼汤(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包括果子狸。
苏东坡吃的果子狸很有可能是他在山林里打到的猎物,或者是别的猎人送给他的猎物。这个猎物又名“牛尾狸”、“玉面狸”,早在《山海经》里就有记载:“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苏东坡不愿自己独享,拎着这玩意去找了当时的黄州太守徐君猷。于是在北方萧萧雪花飘飘的夜晚,在绿蚁新醅酒和红泥小火炉的客厅,苏东坡与徐太守一边欣赏着厨娘的纤纤玉手,一边品尝着果子狸肉涮火锅,那滋味,什么鸡头鹘、通印子鱼与披绵黄雀都得靠边站。
话说回来,鸡头鹘、通印子鱼与披绵黄雀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吃得的。果子狸究竟有多好吃?读过老苏的《送牛尾狸与徐使君》一诗的人们都按捺不住了。先是他老弟苏辙,找机会当了下线,吃完之后也写诗大赞“首如狸,尾如牛,攀条捷险如猱猴。橘柚为浆栗为糇,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简出善自谋,寻踪发窟并执囚,蓄租分散身为羞。松薪瓦甑烝浮浮,压入糟盎肥欲流,熊肪羊酪真比俦。引箸将举讯何尤,无功窃食人所仇。”接下来是苏辙的儿子,也跟着叫好“江国绵蛮登俎味,蒻缸渍畔糁盐醯。坐愚糜殒追时好,嗟汝头颅不自知。獠羞峦错儒庖溽,熊掌大嗤牛尾狸。饫脔羊膀与驼蹠,芳辛咀噍半酣宜。”
审核编辑:落叶半床 精华:落叶半床

 先说“花”,再说“吃”
先说“花”,再说“吃”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