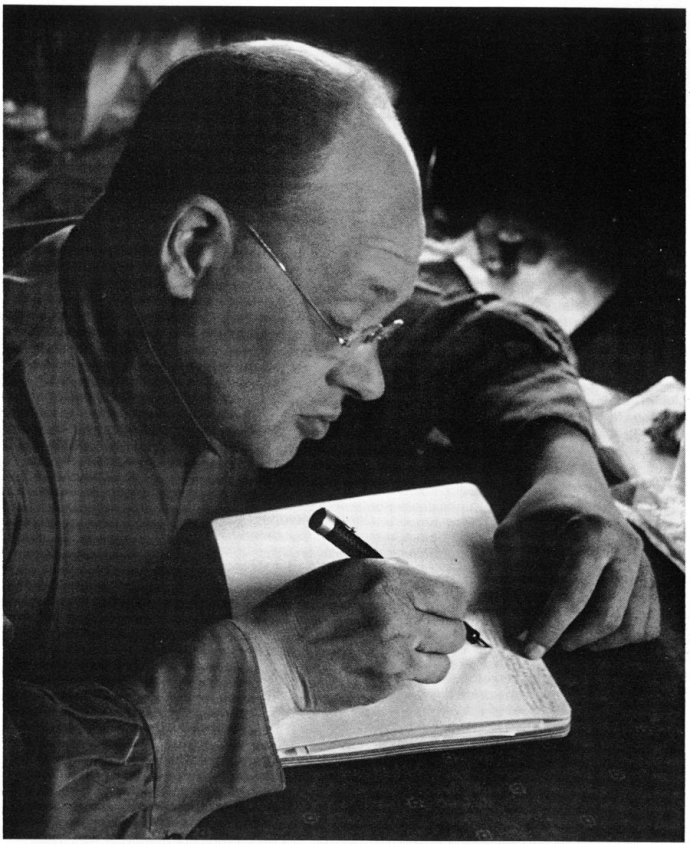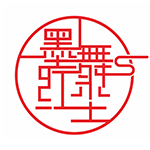我的寻找恍如刚刚走出梦境,方向变得扑朔迷离。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首先弄清楚的是:我是谁?那个人又是谁?
……一只手挟着香烟,另一只手在键盘上敲打。文字一个接一个显现,像黄昏后城市里一盏盏亮起来的灯火。车子奔驰而过,行人忽然在一个句子中间停下来,接着就出现了那只虫子。
想想吧,这是一只昆虫,来自露水充足的田野上,是火树银花的城市吸引了它。离开翠绿的田野,树林深处传出一声乌啼,它有点犹犹豫豫,试探性地盘旋一周,接着停下,然后出其不意地继续奔向城市。一路上,它穿过了车流滚滚的郊区,顶着废气和烟尘前进,绕过第一个红灯,在立交桥和立交桥之间放缓速度,暂停在狭窄的绿化带草丛间喘息,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一道绿化带到另一道绿化的辗转迁徙。当路灯放亮,它忍不住回想起田野上的故乡,在黑夜中嗡嗡低吟。感觉脆弱的时候,它或许需要找个黑暗中的缝隙,躲藏起来,可它更喜欢灯光,喜欢进入灯光之中,升到灯光之上,所以决不会折转身子原路返回。黎明到来,它不得不坚定不移地向前飞翔。
我是我的昆虫。
这只昆虫继续前进,飞过街道拐角的零售店,进入城市的中心。它或许借助着黄昏盘旋的风力,奋力向上;或许贴附在归家者的衣襟底端,进入徐徐上升的电梯,必然地进入楼内明亮宽敞的走廊。然后,当人们昏昏欲睡的那一瞬间,昆虫尾随着微微的光亮侵入房间。只不过谁都没有留意罢了。
温暖的阳光照在那只昆虫身上,窗外的世界越来越静,也越来越远。
接着,它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城市和街道又变回山谷和溪流,四处生长着高大的树木、连绵的灌木丛和柔软的小草。没有一个人,天空中飞着蜻蜓,池塘中水草的阴影里布满蜉蝣,风声细细,带来木叶间昆虫翅膀振荡的回声,一只青蛙清亮地叫了一声,螳螂举起了臂膀,林间的空地上浅红色的蝴蝶如花一般摇曳。那只黑色的蜣螂,头向下俯着,前腿蹬动,后腿抓紧一个几乎有鸡蛋大的粪球,一步步退着向上走。它没有看到前面横亘出地面的尖石子,前功尽弃的预兆。随即,粪球一跳,接着顺坡滚落下去,连蜣螂也被拖了下去。但蜣螂丝毫没有变更路线,决心从头再来。
我是我的昆虫,一只平淡无奇的昆虫。在这个忙忙碌碌、各自专注的世界里,除了获得或失去,谁也不会在乎我的出没,也没有回头的路。没有被惊醒的忧伤,像厚重的甲壳,重重地裹着我的身子。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博尔赫斯微笑着说,随即又毫无把握地补充说,他的梦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看完这篇名叫《另一个人》的小说,然后又从头仔细再看了一遍。其中的那个人,面临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我同时也察觉到自己在惊讶中颤抖。“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博尔赫斯如此说。我若有所失地合上书本。
除了书上说的心理疲劳,失眠引起的幻觉,一定还有什么别的理由,使我在清醒时刻充满失望、惊慌,与此同时,暗暗希望飘向天空深处的浮云都停住,甚至保持固定不变的形状。比如在城市,我们只能通过精细的地图册来认识,一旦踏进其中,密集而混乱的道路就让地址指向不明,使人不知所措,坠入荆棘丛般的迷宫。如果天上的云不变,停在某一天的路上,你怀着渴望往前赶,就一定能看见下面站着的那个人,沉睡的那桩事。世事尘埃,白云苍狗,谁在谁之前出现。我在我的睡眠里走动,翻来覆去地说话,直到眼睛睁开,身前是空荡荡的风,窗外的云朵堆砌如墨色山峦,即将下雨。
香港《大公报》报道,狐狸袭击了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一个养鸡场,所有的母鸡被吃光。剩下的那只公鸡,鸡冠高耸,叫詹尼,一个骤然间失去所有后宫的、悲伤的国王。报纸上说,詹尼没有郁郁终老的概念,几天后,它不但每天生鸡蛋,而且还开始孵蛋。此事让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感到不解,初步判定,为了救亡图存,是詹尼变性的原因。专家特别指出,这项研究将有助解释“鸡先还是蛋先”的难题。
我不知道这和我正在考虑的事情有没有联系。现在的报纸上,谁也不可能奢求找到自己所想所需的事实,包括寻人启事。
笔记一则:
“如果有人梦中曾经去过天堂,并且得到一枝花,作为曾到过天堂的见证。而当他醒来时,发现这枝花就在他的手中……那么,将会是什么情景?”
——科勒律治之花。
到底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这朵带着天堂雨露的花,逾越了真实与幻想的间隔,既美丽神奇,又有一种形而上的恐怖。
有一天,我在楼下遇到邻居男人。当时他扛着一台电视机,说要去出差。他的脸上有一层闪闪发亮的油光,所以才跨出电梯门口,一只苍蝇就飞落下来,停在他的鼻子上。春分的那天,隔壁这家人又是焚香,又是烧蜡,弄得乌烟瘴气。婷婷和我躲在门后,低声争论这是什么地方的风俗。他们在屋子时而悄无声息,时而发出砰砰的响声。婷婷说,这声音像是在打小人。响声停止后,我们隐约听见女人的嚎哭声。
我进电梯,徐徐上升的过程中,看见壁上写着不许在电梯里小便的字样,但是写的人已经失踪,要换了我才懒得这样。被损害、被侮辱的情形无处不在,就像太阳要出来一样。电梯门缓缓打开,在走廊上,我见到邻居的女人坐在门口,脸色又青又白。据说,痛苦令女人脸色发青,愤怒时,她们又脸色发白,但我最清楚,脸色又青又白的女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里发神经。我一边开门,一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刚刚遇见他了,说要出差。正在发呆的女人听到话声,回过神来,骂道:不要脸的,和我离婚,还要搬走那么旧的电视机。
我还是担心出点什么事,就把门开着。也许是暮色渐浓,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的故乡,曾经的事。后来,电停了,透过走廊的窗,可以看见一轮明月挂在上面,银白的光顺着过道流动。她突然说了一句什么,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但知道这是广泛流传江南的古老禁忌,大意是:女人在流星下梳头,其夫必暴卒于黎明前。她又说,很多夜晚,她就这样手握木梳,坐在窗下,等待着流星的出现。当流星真的出现,她反而犹豫起来,不知道应该梳头,还是许个美好的愿望。她说这样的感受,真是一种煎熬。
在烛光下,我们坐在走廊里继续说着话。她说,在乡下,常常都会停电。
我说,小时侯,我就住在城市东边那座山下的村庄里,有月光的夜晚,爬到屋顶上,可以看见一只狐狸带着几只小狐狸在山岗上奔跑。她说,一切都像在昨天。那时,她放学回家,走在雨后的田埂上,看见趴在草叶间的青蛙,扑通扑通跳进田里。后来,青蛙越来越少了。男人们在黄昏中叹息,说人口多,田地不够种了。他们丢下农具,顺着乡村公路进城。身后跟着更多的人,像一串顺着木头往前爬的蚂蚁,漠然迁徙。田地都留给了老人和孩子,于是不少都空荒着,长满了草。重新提起昨天的忧伤,还是如此刻骨铭心。其实在天黑之前,她已经开始忧伤。
风在地板上沙沙地经过。烛光灭了。她接着往下说。像是一个人平躺着河底下,发出的声音流动着,穿越黑暗中的空气,时而有越过障碍的微微转折和起伏。叙述乡村的稻田里,稻草人拖着影子站在长满小草和野花的田里。然后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动不动地挤在车厢里,穿过滚滚的尘土奔向城市。一切都在离开,壮年的男人,成熟的女人,先是一个月,又是一个夏天。最后,一个女孩,在村庄停电夜晚的第二天,也默无声息地穿过村庄,穿过长满野草的田地,爬上一辆过路的车,进入另一种生活。

 浮云向天空飘去
浮云向天空飘去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