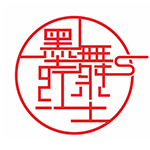父亲说罢,便抬头看天。我也赶忙抬头看天。天上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片云彩悠悠飘过,还有一只老鹰在天上盘旋。最显眼的,就是太阳明晃晃照着。它每天走着固定的线路,东升西落,西落东升,弄得天黑天亮,天亮天黑。老师说,这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可我明明看见太阳自己在天上跑,脚下的大地根本就不动。爷爷说,太阳是一个岁数很大很大的白胡子老头,赶着八匹大马拉着的“太阳车”在天上跑,播种生命,也收割生命。我更相信爷爷的说法。
可我眼下顾不上多想“太阳车”,必须面对父亲下的命令。我有点奇怪地望着他。在此之前,上树这种磨烂裤子还容易摔下来摔个七死八活的顽劣行径,父亲是绝对不允许干的,尽管每天照爬不误,可都是偷偷干。现在父亲却破天荒命我上树,让我感到吃惊,也受宠若惊。可上树却是为了给他砍树栽子“种棺材”,又唬得我心里直发毛,于是迟疑着。父亲瞭我一眼说,十年树木,到时候一口棺材就有了,要是有福气再活二十年,我和你妈俩人的就都有了,不省得你和你兄弟发愁买木材了?我心里还是很拧,却不得不遵命而行。
村里人原来种的杨树都是小叶杨,也叫甜叶杨。杏花雨时节,甜叶杨生出的鲜嫩叶子煮熟后可以当菜吃,与之为伍的还有没炸絮前的柳絮,绿莹莹的榆钱,白冬冬的槐花,都是人们填肚子的宝贝。正因为甜叶杨是甜的,那些长着长长触须、背部有白点子的“龙虱子”(星天牛),便特别爱欺负它们,把又白又胖的幼虫种在它们的树干里,没明没夜在里边啃咬,从树旁走过就能听见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些光吃不动养得白胖的家伙,还把锯末一样的粪便堆积在虫洞口。甜叶杨竟然也会哭,流着黑黄色的眼泪。可眼泪抵挡不了杀戮,甜叶杨的躯干最终被蛀得窟窟窿窿,表皮疙瘩暴痂,黑如焦炭,根本不能当木材用,只配劈了当柴烧。甜叶杨成为啄木鸟最爱光顾的树,它们两只爪子抓着树干上下左右移动,边用又长又硬的嘴梆梆梆地啄击,声音激越如鼓,传得很远很远。
“北京杨”和“钻天杨”是后来从外地引进的优种杨。“钻天杨”其实也不咋样,虽然长得高,可离地没多高就分杈,光顾长树冠了,又稠又密的树枝很紧密地往一块凑,凑得跟没有笔杆的毛笔尖一样。作为防风林带的树或者风景树,或许很理想,作为木材树,就不太敢恭维了。“北京杨”则大不相同,把生长的精力放在树身上,长得又直又高,树身也粗,树杈却没多少,枝条平伸着长,舒朗,简朴,好看。春天时,“北京杨”先吐出一树冠毛毛虫那样垂挂的酡红色花穗,然后长出正面黑绿、背面灰白的叶子,风一吹动,翻一树白色的小手,哗啦啦鼓掌。它们很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把苦味藏在身体内,使得人们不敢吃它的叶子,也使得“龙虱子”退避三舍,因此保养出灰绿色的光滑树皮。抑或是光滑的树皮使得“龙虱子”无懈可击,由此而自保。父亲是一米八还多的大个子,大个子死后需要一口大棺材,大棺材需要大的树木来做成,“北京杨”恰好堪此重任。有一点不妙的是,“北京杨”光溜溜的树皮,难住了我们这些好爬树的野小子,一些伙伴只能望而却步。可父亲知道我爬树的能耐,所以让我上树去砍“北京杨”树栽子。
腰后别一把镰刀,费劲爬上一棵“北京杨”,骑在树杈上,拣一枝大小适中的树枝下了镰,砍一下,树枝便喊“疼”,再砍一下,又喊“疼”,我发狠连砍了几下,它连声喊疼、疼、疼。我暗暗对它说,伙计,砍下你是为了让你长成一棵独立的树,即使这棵树明天就砍了,你还是这棵树生命的延续,你就消停了吧。树枝便缄口噤声,不再喊疼。我把砍下的树枝扔下去,然后下树,将树枝去头,截短成三尺左右,拿着回家。
放下饭碗后,父亲掂了把镢头,拿了树栽子,到我家院子底下的小河沟去栽树,我也随后跟来,看看能不能给父亲打打下手。在父亲面前,我一直是个乖孩子,脱离开了他的视线,我才疯得像捉拿不住的孙猴子。这是河槽处的一个石头岩坎下,夏天下雨发大水,像野马群奔腾的洪水从岩坎上拥挤着扑下来,形成一丈多高的飞瀑,在崖坎下冲出一个很大的坑,将泥沙和河卵石都推到了四周。父亲在靠院子这边的泥沙上选择好地方,刨栽树的坑。这地方不错,足以长起一棵好树。泥沙里混杂着很多好多石头,父亲转着圈刨坑,刨起的石头,我便搬起来扔到河道里。坑很快就刨好,父亲把树栽子放进去,我用手扶正不让歪斜,父亲将泥沙扒回坑内,填一层就用脚踩瓷实。树栽好后,我在崖坎的背阴处挖了一团消雪时浸湿的淤泥,裹在树栽子顶部,又找来纸和绳子,包住泥巴并拴紧,这样可以避免树栽子里的水分跑掉。父亲对我这个举动很满意,一龇牙赏给我一个赞许的浅笑。
我仰脸偷看他难得一见赏我的笑脸,抬头之间太阳一下刺疼了我的双目,我听见“太阳车”从天空驶过发出的轰隆隆的巨响。我努力穿过太阳刺眼的光芒,看见太阳公公长而蓬乱的头发、胡子,都白亮如雪,同时看见他驾驶的“太阳车”好生古怪,前半部是播种机,后半部是收割机,二者组合成一个整体,在拉车的八匹大马的奋力奔跑中,轰隆隆地向前疾驰,一刻不停地播种着生命,也一刻不停地收割着生命。播种与收割的生命囊括天下所有的生灵,高贵者如人,低贱者如花草鱼鸟、百兽虫蚁。收割这一块,次序有点杂乱,有的收割得早,有的收割得迟,但其多层次收割的精密却不容置疑,任何一个生命也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生命也没有逃脱的侥幸。父亲比我吃的盐多,经见的世面当然也多,也一定听过爷爷讲过“太阳车”,自然知道“太阳车”收割生命的无情,所以才让我给他砍树栽子,给自己种“棺材树”。
树栽子发芽成活是明明白白的,生长却在不知不觉之间。用肉眼看,你永远看不见它生长,可它既得其土,又得其水,速度很快地往高处窜,往粗里发。我上初中时,它已长成一棵两三丈高的树,连爱占高枝的喜鹊都在它上面做了窝。可奇了怪了,在树杈的下方一米处,偏偏被“龙虱子”的幼虫钻了一个洞,向外淌着黄褐色的水。这对“北京杨”来说,绝对是个例外,可偏偏被父亲种的“棺材树”摊上了。要说,啄木鸟也来帮过忙,眼看着梆梆梆、梆梆梆在那里忙活,洞口也明显啄大了,虫子应该掏出来吃掉了,可这个洞就是不闭合,像一个挖去眼珠子黑洞洞的眼眶,嵌在大树上。要命的是,洞口的方向朝南,夏天一刮南风,大雨就会下个不停,风卷着雨水灌进树洞里,使沤得发黑的水直往外淌。父亲从地里下工回来,常常擎着烟袋去看那个洞,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本家二大爷、三大爷担水打此路过,都打招呼,这洞再不处理,就会从树中心一直烂下去了,这棵树就毁了。可父亲左看右看想不出摆治这个洞的办法。星期天我从学校回来,父亲让我想想办法。我心里揣度,爬树上到树杈,弯腰够不着那个洞;爬到树洞的地方,抱着树手腾不出来还是摆治这个洞。我最终帮父亲想出个办法:架梯子上到一定高度,用一根长木杆绑上喂猪用的铁勺子,抄上生石灰粉、硫磺面和农药六六六粉的混合物,一点一点放进树洞里,估计就可以治好了。我们果然这样做了,打此后,树洞里再没往外流黑水。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那个树洞还是有继续长大的迹象,变成小碗碗口那么大,可树中心到底有没有往下烂,就说不清楚了。好在,树活的是一张皮,只要皮是好的,不影响树的生长,父亲的“棺材树”长成两个人才能合围的大树。

 太阳车
太阳车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