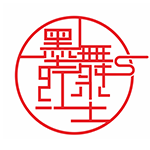余华在散文集《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里讲他曾帮牙医沈师傅洗照片,不小心把沈师傅最满意的底片掉地上摔碎了。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流行多年,“底片”已变得遥远而陌生,文字好像打开了一道关闭多年的门扉,与底片和照相有关的记忆便在夜色里活跃起来。
打记事起,关村红华公园入口的台阶旁边就有一个二层小楼的照相馆,就是现在立有“三线记忆小镇”几个大字的旁边,照相馆门外有一圈平地,地面用亚克力砖砌了一个圆形图案,相馆里的墙面挂着夸张艳丽的风景画。无数张无数个家庭的照片,就是依托这些风景画做的背景。照相馆毗邻当时唯一的公园,公园左边是俱乐部,那时候还有电影院,卖票观影,也有篮球场和游泳池,很少对外开放。
家里第一张彩色照片正是出自那个照相馆,三姐姐从小勤劳,深得父亲喜欢,对她偏爱多一些,要求也容易满足,照了全家照,还让她穿着彝族衣服,百褶裙铺开照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单人照。八十年代的微笑一直定格在妈妈用木架做的相框里。那张照片记录了三姐姐初成少女的模样,如今已过五十岁。在那次拍照之前家里也照过为数不多的照片,都是一寸、二寸的白黑照,和现在的工作证件照一般大小。黑白照有一种气质,皮肤细腻,人在照片里有着超越平常的深邃,是彩照达不到的宁静、神秘和高贵。
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有记忆起父母已近中年,如果不是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穿“军服”的照片,永远不会知道她年轻时的样子。军服是走村串户的照相师傅随身携带的道具,在装了相机、交卷的工具包里,还装着镜子、手绢、衬衣等照相用的装备,军服算得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饰物。母亲那张唯一年轻时的照片,两根长长的辫子分在左右,瘦削的脸庞有着青春之光,写着她对人世的憧憬和向往。生活中现实的母亲一直以黑色头纱包头,系着粗布围裙,身材结实偏胖。她的打扮与小凉山地区无数母亲的打扮一样,即使到城里生活多年,也没有更多变化可见。
童年仅拍过两次照片,还是合影,一张和小姐姐在一起照的,那时约四五岁,在照片里眉头紧锁,拧成一个川字,大圆脸和婴儿肥把眼睛挤得紧凑,晃眼一看似在深思了不起的大事。手里拿着一团卷成“牡丹”的白色纱巾,如果不是黑白照,那纱巾应该是红色,红色和粉红也是那个年代颜色的主流。另一张和三姐姐,旁边还站了一个清秀的女子,曾经以为是六姨娘,经三姐姐辨认是坎下那家的,不到二十岁便远嫁外乡了。那些年村里的姑娘一到十五六岁,便被媒人或同村姐妹说去了平原大坝。不像现在,村里没有姑娘,只有老人。那张合影里的我仍然手握纱巾,仍然眉头紧锁。
其实还拍过一张照片的,和外婆的合影,那张照片后来还见过几次,照片里还有小姐姐,大表弟和表妹,那时候最小的表弟还没生出来。外婆清瘦,骨子里有一种旧式妇女的威严,也有淳朴的慈祥。外婆是读二年级上册那年走的,她躺在门板上白纸覆面的时间很短,更多时候是带着我们院子割猪草,把老腐的菜叶取下来,或者围着灶头煮猪草、做饭。外婆信佛,每年要和姑婆去峨眉山朝山,朝山会带回来普贤菩萨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彩色的。
菜园里选了一个平整的地方,外婆坐在高板凳上,旁边依次坐着大表弟、表妹,外婆抱着我,小姐姐靠着外婆,小孩都光着脚,卷着裤腿,头发乱糟糟的。后来那张照片找不见了,外婆的样子也快想不起来了,小姐姐走了三十多年。
照片是走村的摄影师照的,他们背着相机到一个个偏远的村子,为需要的人拍照,下一次来村里的时候顺便收钱,给不上钱的人家,给粮食也行,因此摄影师返程的包里还会多出来腊肉、粮食和药材。
后来举家搬到当时唯一的镇上,小镇有唯一的巷道,宽可以过一辆大汽车。两边是垂直千米的悬崖,一边的民房贴着山崖,一边的民房垂立流经小镇的野牛河,河流清澈,水声浩荡,野牛河也是贴着山崖前行,流到二中那边的火车桥下与大渡河汇合。
镇上也有一家照相馆,半面店铺临街,里面靠墙完全是悬崖的岩壁。上学和放学都会路过那家照相馆,店门的橱窗挂着明星照,也有拍得比较漂亮的生活照。刚入青春期的姑娘把筷子烧烫,烫出卷卷发,亲手编织的高领毛衣遮着光洁的脖子。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一张张照片上。
第一次有属于自己的照片已到城里读书。和平街上有了一家江记相馆,江师傅到学校来给毕业生拍照,那时候的江师傅比现在江记相馆的江师傅还年轻。学校给学生发饭票也发面票,面票饭票可以攒下在学校外面的小卖部换成钱。所以那天拍过毕业照后,找江师傅照相的学生很多。那时的大渡河还有着汹涌的河水,澎湃的河面,河岸有大面积的黄白色沙滩,河中有激荡的漂木,河对岸的城区还没有高楼。枯水季节,大渡河两岸多出来许多采集沙金的老百姓,几个人摇一个木架子,把散落在沙滩上的碎金摇集在沙砾中,用水银提炼出来。学生以大渡河做背景,站在沙滩和鹅卵石上,等着相机咔嚓一声。那时还没流行剪刀手,也没人会喊茄子。双手垂臂,笑容僵持。
记不得当时是什么心理,就跟着同学拍了照片,照片拍完以后想起自己根本没有钱。怎么就稀里糊涂拍照了呢?紧张、忐忑、懊悔,复杂的情绪充斥着年少的心灵。惶恐,不安,即使现在也不能描述那种感觉。胶卷要等几天才能洗出来,因为不能立即取,不需要马上交钱。有死里逃生的后怕。
三十多年前的和平城区和小镇一样,也仅有一条街,从铁索和木板构成的吊桥过去,桥头还有一个大型水塔,街道两边排着高大的梧桐树,浓荫遮挡着街道,地面铺着坚实耐磨的三合土,缝隙填着沥青。那时的江记相馆在老街上,因为那次拍照和那张没有钱取的照片,那条街成为有形的压力和负担,压得年少的我喘不过气来,又不敢给人讲,只要路过就会紧张、脸红、淌汗。一张照片、一元五角钱,成为那个年龄的不可承受之轻。
甚至偷偷祈祷拍照不成功,希望胶卷曝光了。可它却被洗出来放在照相馆窗台正中的盒子里,与一堆装了相片待取的白纸黏的小袋子码在一起。一次陪同学去取照片看见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与我近距离对视的瞬间,竟然产生了濒临死亡的窒息感。怎么跟着同学离开相馆已经不记得,回到学校很多天都魂不守舍,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上街。
一直拖到放暑假回到老家。为了筹钱,割完了猪草便去林子里摘五倍子和鸢头鸡娃,卖给到山里来收药材的商贩,一个假期过去才凑够了取照片的钱。开学到城里,第一时间就去相馆把照片取了出来,突然的轻松使人想流泪。袋子里装了两张黑白一寸单人照,一张底片。
底片是一种奇特的存在,好似封存着无数黑与白与灰的秘密,底片把人和物的某个瞬间存放在里面,历经时光和变化仍然守持着按下那刻的光影。需要的时候加洗出来,便有水落石出的清晰和自证清白。
那两张照片和底片不知何时遗失,也记不得照片里的自己是啥样。但因那次照相而承受的情绪给生命留下太深的印痕,自此至今,仍然不敢做能力之外的事,不敢消费支付不起的生活。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多了起来,照相不再是稀罕事。照相馆开始承接加洗照片的业务。关村那家照相馆不知啥时也没了,原址被平掉后种了树,树木对空间的弥补超过土石建筑,能很快消弭时空的变化。
早年也先后买过几台相机,但受那张照片的影响,始终不愿意拍照,相机也只是用来拍点花花草草和旅途风景。近十年来,智能手机越来越先进,摄像头早已具备和满足普通照相需求,对照相的取舍变得容易,随意而自在。而和胶卷有关的产业破产的破产、兼并的兼并,成为一种遗憾,一声叹息。只有相机还在更加专业的路上前进。

 【流年】流年似水
【流年】流年似水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