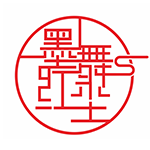虱子的故事
很早以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田里头的燕麦,人里头的贼,身上的虱子。这三样东西,一个拔不尽,一个除不掉,一个捉不完。农家人年年除草,总是除不尽麦地里的燕麦,不是农人不勤快,实际是造物主高明,燕麦为了适应传宗接代,植株上的果实不在同一时间成熟,它是熟一粒落一粒,休眠期也不同,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下一代的传承和沿袭。而做贼的大都是贫穷潦倒,无法生存的人,或者是一些胸怀鬼胎、好吃懒做之徒,还有一种就是逼上梁山的英雄,他们在人世依靠正常的生存法则,已经无法维持和维护生命,只好落草为寇,担着贼的名声,过着裤带上别着脑袋的营生。而虱子作为堂堂七尺之躯的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蟊虫而已,但是,它用锲而不舍的毅力,摧毁了人类的忍耐,才让人感觉愈发的心烦意乱,有狠无处使,有气无处出。
虱子是天下最无耻的东西,无论你怎样讨厌它、憎恶它,它依然不离不弃的伴随着你、依附在你的身上、借助你的体温温暖着自己,用叮你、咬你、恶心你的方式,完成喂养自己的职责,哪怕你有倒拔垂柳的力气,愚公移山的恒心,对于虱子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的事情,它丝毫不会畏惧你,依然恬不知耻趴在你的身上生生息息,代代繁衍。
在虱子的眼里,人其实就不是人。这么硕大无朋的物件,虱子永远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像我们面对一座大山。任它爬遍你的周身、走遍你的坎坎坷坷,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你的形态和模样。不只是因为它生存在阴暗的环境中,更重要的是你的确比它高大得太多太多了。在它的“心”里,人类就是它无边无垠的土地,是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财富之源、生命之源。那么,所有的生存和繁衍就只能在这里完成,也只能在这里完成。当你辛辛苦苦的拿着铣把䦆头在地上为生活劳作时,它丝毫不会感激,也不会有任何知觉,它们在你身体的阴暗处,习以为常的料理着自己的生活、干着自己的活生——无度的嗜血或者尽情的交媾。
多么贫瘠的土地也不乏生命的踪迹;多么瘦弱的身体也会有虱子的寄生。这就是我们绞尽脑汁,耗尽体力也不想离开的世界另一种版本。好死不如赖活着,越是贫困越有期盼。总想出人头地,总是寄人篱下。这就是你想坚强活下去的动力。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村子里有位老人的儿子因工作原因,当兵二十年未归。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他想把二十年萦绕于心的孝敬之心,合盘端出来报答养育之恩。问母亲想吃点什么?母亲颤颤巍巍、嗫嗫嚅嚅地说:儿呀!妈就有时候想吃点好的,有时候不想吃点不好的。
吃成了这位老人今生的唯一,尤其是吃好的。
在这里我无意责备这个老年的、贫困的母亲的真实诉求。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把她打磨成了老人,也磨消了年轻时的意志。之前的岁月里,她把全身心精力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现在面对儿子——这一颗她生命里的丰硕果实时,这个要求是真实的、朴素的,再也不是高大上,再也不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虚无缥缈。生命的首要不就是以艰辛地劳动喂养自己的过程吗?有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喂养了自己,喂养了众生;而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从不想去劳动,却想无尽的拥有,世上饿殍遍野,他因此而盆满钵溢。盆子里盛着的是被迫而逝的冤魂,鉢里流淌的是被压榨而死的血肉。
这些人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远远在区区虱子之上。他们的名字叫贪官。他们道貌岸然,手握权力的利刃,张牙舞爪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像嗜血的虱子一样,趴在社会和人民的肌体上贪婪的榨取、无度地吮吸。更可恶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自恃强悍的国家也是这样,爬在西半球肥沃的土地上,猎犬一样虎视眈眈的扫视着世界,只想自己作威作福,容不得别国体壮腰圆。历史就变成了一步榨取与反榨取、吮吸与反吮吸、侵略与反侵略的教科书。
可悲的人类,从原始一路走来,一路血雨腥风。
虱子嗜血是天命所归,它遵从的是造物者的意图。人类偌大的身躯,喂养一群虱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是它污浊了健康的躯体,还要传播一些疾病,这就是它罪恶的渊薮,也是让我们更加讨厌它的理由。
俗话说:穷虮子饿虱子。人的生活越是紧迫,虮子虱子就分外的多。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穷的标准是什么?穷的标准无疑是饥寒交迫,缺衣少食。
我的童年乃至少年就是在贫穷中度过的。那个时代,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穷,是整个社会的贫穷。那个时代不是人们不勤快,而是整个社会和人民都竭尽全能的奋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是破烂的山河。国家一穷二白,人民一穷二白。科学技术、机械制造从零开始,贫穷能够激发起人民奋发的意志,贫穷却难以治疗身体的饥寒交迫。
贫穷导致了虮子虱子的变多。几乎是在睁眼闭眼之间,脑屏上总能闪现出这样的画面:工闲的母亲坐在门前的树荫下,抱着儿女脑袋,分开髹如毡毯的头发,像在田里薅草一样,掐死隐藏在头发里吃得膀大腰圆的虱子;夜晚昏暗的油灯下,父亲或者母亲总是翻开孩子破旧的棉袄,认真的搜寻或掐死藏在隐秘处的虱子。而一个壮年的男人站在一群男人女人的堆里,翻开肮脏破旧的裤腰掐虱子,也是再稀松平常,无伤大雅的事了;那些成年的妇女互相抱着脑袋掐虱子,几乎成了农闲工休时的一种娱乐,沾满黑血的指甲盖,让今天的人看到必定作呕不止。
在我们村子里,虱子最多的人首推庄三爷,他是大队油坊的会计,每天在油坊里干活,衣服外面沾满了油渍,久而久之就像一件闪闪发亮的皮衣。他住在油坊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每天晨起干完一些必要的营生后,太阳便以冬天最大的热情光顾了油坊向阳的门面。庄爷没有时间耐心细致的捉虱子,那样会耽误他的正事。他把明秀秀的棉袄脱下来,翻开里子用一把糜草扎的笤帚,狠狠地扫一遍,地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类似于麻籽大小的东西蠕蠕而动。然后,他用脚底胡乱地踩几下,就出现“啵唧啵唧”的声音,这些声音,与其说是生命罹难的垂死叫嚣,不如说是死亡之神的大声嚎啕。具体他身上有多少虱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的肉甜,虱子爱吃。他执掌着村子里油坊的大权,在村子里韵事不断,他肉皮的甜与不甜,也只有和他有过切肤之交的人才知道。其他人知道的,只能是他的超越常人的多虱子和勾连女人的黑能力了。
按照庄爷的理论推断,我的肉皮也是甜的。甜的依据就是虽超不过庄爷,但也不少。小学时,我的食宿都在父母的呵护之下,这时候,我身上虱子多的优势还没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上了高中离开父母,住在学校三间大的大通炕上,才渐渐地展现出这一特征来。那个大通炕,至少住着十多个半大小伙,炕上铺的是厚厚的麦草,麦草之上才是我们简陋的毛毡被子,这是一个交流和繁殖虱子的最佳温床。一个挨着一个的铺窝,一字儿排在一个长达十米的土炕上,虱子可以在我们注意和不注意的情况下自由的窜来窜去,没有声音,也没有痕迹。想吃谁的血就吃谁的血,想和谁有肌肤之亲就和谁亲密无间的住到一起。虱子是我们宿舍里最自由开放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不至于在一棵树上吊死。
它是我们少年大家庭里的一员,与我们同欢乐共自在。
我不知道,在我们被仓促的铃声召唤了去上课的时候,它们寂寞不寂寞?孤独不孤独?有个别一些机灵的家伙例外,它们早已或者压根就潜伏在我们的衣服中,随同你一起上操、听课、参与我的一切活动。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认真听讲,陶醉于老师触动灵魂的讲述时,就会感觉身上的某个部位有一只我随身携带的生命在移动,还时不时撩拨我神经的琴弦,让我奇痒难忍、好不自在。我不知道老师的讲课是不是也触动了它的什么?它在我的衣服之下,身体之上,显得格外激动,总是导致我离神分心。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手伸进目标明确的活动区域,几乎是手到必擒。我羞于把这样的物什拿出来昭示在日光之下,大众之前,只能在擒拿到手后就地正法。我对它采取暴力处决的方式,极其简单轻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轻轻一捻,虱子马上就会粉身碎骨。我弄不清我在高中的课堂上脸红心跳的处决了多少个不守规矩的虱子?但是,我决心要和这个微不足道的家伙血战到底。

 虱子的故事
虱子的故事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