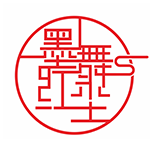A
等待,是一份浓浓的思念与牵挂。
怀人,是生长在乡野村口的一道醉美风景。
耳边常响起童年时唱过的歌谣《大路口》:“大路榜榜,小路弯弯,我站在路口把眼望穿。盼人儿盼了三年半,见不着人儿把泪流干。”生活中,好多人都经历过等人的情景,也经历过被人等候的滋味。不管是妻子回了娘家,半月不回;男人外出打工,半年不回;另一方的思念与牵挂,站在门口与村口的等待,都是一杯醇醇的酒,一杯浓浓的乡愁。那酒浇进民歌,那愁融入乡音,来年就会在乡村的田野上疯长。
首先听到有关思夫怀人的故事,是奶奶的。我生下时,没见过奶奶,更没见过爷爷。有关奶奶的故事是娘喧的。娘说奶奶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很厉害的当家婆,三个儿媳,十几个孙子,那么大的一个穷家,还要一个锅里搅勺子,愣是让奶奶管的井井有条,孙子们碗里的稀稠,基本匀适,概没有老大的娃吃饱了,老三的娃还饿着,这种偏三向四的事儿。娘说,她们主娌几个,都很怕奶奶,主娌之间即便不和,也不敢当着奶奶的面吵架,更不敢提分家的事儿。儿子们分家另过,是奶奶不在了才分的。奶奶当家,是因为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爷爷肩上。爷爷年轻时,给山那边打柴沟的老牧主放羊为生。爷爷一年回来一次。每年腊月门上,奶奶就天天站在村口等。有一年,直等到腊月底,等来的却是爷爷的噩耗。爷爷回家,路过乌鞘岭时,天下大雪,被活活地冻死在了一个山旮旯里。爷爷是想蹲在山湾湾里避雪,等雪停了再走路的。不料,自蹲下,头缩在皮袄里,就再没起来,冻僵了。刚踏过四十门坎的人啊,说没就没了。后来,是一个放羊的羊倌,捎来了信儿,才找到爷爷的尸体。但那时穷,父亲兄弟三个,没有办法把爷爷拉回来。直到现在,我们的祖坟里,埋的只是从那个山弯里招回的象征爷爷魂魄的一把土。爷爷的尸骨,永远埋在那个山弯里。奶奶的思念也永远留在了那个山弯里。
奶奶穷,没给娘传下什么,只给娘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件是物质的,盛针头线脑的布篮子。我在散文《母亲的布篮子》(已收入散文集《村庄亦或逃亡》,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里,专门写过。一件是精神的,怀夫等人的滋味。父亲,还有大大,三爹,弟兄三个,一夜间被霸居青海的马步青抓去当了兵。娘就站在奶奶站过的村口等。大妈、三妈也等。娘等时,手头有时拿着针线活,给父亲衲的一个鞋底,或一个鞋膀什么的。衲着衲着,那鞋底儿也就成了遮阳的手篷,遮在了娘的额头上。娘直等了两年。娘、大妈、三妈都比奶奶幸福,终于把父亲兄弟三个等回来了。父亲和大大、三爹吃不了马家兵的苦,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各偷骑一匹马,超小道从青海跑回来了。据父亲说,解放后,那三匹马成了生产队种地拉田的得力牲口。从此,父亲一生再没出过门,不要说远门,连两里地外的定宁寨子,都没去过,更不要说二十里外的古浪县城了。一杆鞭子,一张犁铧,一对黄牛,一把铁锹,一个铡刀,陪伴了父亲一生。我曾问过父亲,你给国民党当兵,放过枪,打过人不?父亲说,放啊,朝天放,土匪也是农民的儿子,怎么能穷人打穷人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挨饿时节,家家的男人出门讨饭了,唯父亲坚守乡野,硬可挖地三尺找草根,也不出门讨饭。不为脸面,不为别的,父亲就怕他出了门,娘站在村口等。我不相信父亲不逃饭的理由。但到七十年代中期,村子里又出现了逃饭潮,这次我相信了,家里母亲、大嫂、三哥,还有我,都出去逃过饭,但父亲仍然坚不出门,信守着他内心的东西。
1978年,时来运转,全晨光村,一个班四十多人,就我一人考到了古浪一中念书,七八个考到了定宁中学(那时设高中),其它的,都无书念,回家种地了。对我而言,到古浪一中上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了远门。第一次,我失去了上学的伴儿,成了独行侠。每到礼拜天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馍馍独往县城,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背着空包包独自回家,二十多里山路,有时放学迟,出了古浪县城,过了干河(古浪河),怕太阳落山,怕路边和山坡上的野坟鼓堆,就从长流渠一路小跑着跑回了家。开始几周,娘就在羊路口等我。我还没进村,远远的,就看见娘一人在羊路口上站着,迎风里,娘的衣襟在飘,头发在飘,近了,头发上粘着几根金黄的麦草。每每此时,幸福与满足就荡漾在了娘的脸上,而我的胆子也就一下子壮了。但娘等了几次,见我习惯了山路,不害怕了,就再不等了。每见我回来,装着的都是手提背篓在柴草堆上撕柴草,生火做饭的情景。
B
等待,怀人,相似的图景,其实早就出现在《诗经》的时代。
《卷耳》开言就道:“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卷耳,我童年时叫苍耳子。果实如沙枣核大小,上有钩刺。嫩叶可食,苍耳入药。春天,在阳光暧照的青山坡上,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小花,点缀在满山坡的绿草之中。一个女子,左胳膊肘儿上挂着一只浅浅的篮子,走走停停,她时而俯身采摘苍耳子嫩叶,时而拧立高处遥望远方。她的爱人骑着一匹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出了远门,承负徭役去了。她想起了远行的丈夫。不由得停了手中的活儿。一阵清风掠动了脚下的绿草,她才注意到,采了半天,才采了浅浅的一小篮。反正是心不在焉了,她索性卸下提篮,放在空荡荡的大路边上,仿佛把一切的思念都放在了这里。夫妻两处,远隔千山万水,维系着彼此神思的,只有这条蜿蜓曲折的路了。《诗经》卷耳中的这路,好象我童年时家门前的羊路口。
每每看到此景,《卷耳》中的女子就会幻化成我娘,默默地站在村口,等待在外苦役的父亲。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我童年熟悉的民歌《大路口》,而是两千年前的民歌《卷耳》:“山坡高高,大路弯弯\\山坡上长满了苍耳子草\\苍耳菜好吃我无心挑\\半天里只挑了一浅筐\\见不着心上人我心发慌\\把筐儿撂到了大路榜。”那余音,苍凉,辽远,似天籁,又如马蹄的踢踏声,从山那边传来。
这份浓浓的怀人之情,如一条溪流,就这样从远古的暮色炊烟里轻轻地流淌着。从《诗经》的时代流进了唐朝。唐朝诗人张仲素写过一首《春闺思》:“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简直就是《卷耳》的翻版。只不过思夫的女子手中,一个在采苍耳子,一个在采桑叶儿。一个等在大路边,一个等在郊野上。早上出门,采桑女还在回味着昨夜的梦,梦中,她去了关河万里的“渔阳”,与戌边的夫君相见,悲喜交加的情景,仍萦绕在脑际。而眼前的风光,郊野的垂柳千丝万絮,随风摇曳,青青的桑叶悠荡枝头,浓密茂盛,更勾起了采桑女的“千思万绪”,采桑女手提竹笼而立,想着想着,就忘了采摘桑叶。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这是一尊尊站立在时空邃道或怀人驿站上的美丽雕像!上古时代的女子,唐朝时的妇人,当代的我娘,都因思夫而忘了采卷耳,采桑叶,手中的针线活,站在大路边,站在村口旁。这其间相隔千年,而人的感情经历竟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停地流淌。
C
但《卷耳》,比我童年时的民歌《大路口》,更有风味。对于等待、怀人的情景,民歌若用单一的场景,单一的女声,唱到女人们失神地站到大路边上,也就表现到极致了。再现,再唱,无疑会显得累赘与多余。《诗经》时代的先民,在表达情感时,是绝顶聪明睿智的。《卷耳》在女子把筐篮丢在大路边上,孤独地站立路口时,相思的场景突然转折了。就象今天的电影,导演突然把画面由大路口切换到了山那边另一个场景上。在这个场景上,思夫的女子不见了,而是女子想像出来的夫君骑着马子急急往家赶的情景。想像中,夫君也同样在怀人,在思念着她,念想得情深意浓。恨不得让快马长了翅膀,飞回老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卷耳》是中国电影、电视剧本的鼻祖,她用民歌的语言,切换式描写了两个场景,景很短,情却很长。民歌很短,故事却很长。《卷耳》很短,历史却很长。

 快马的蹄音响在心上
快马的蹄音响在心上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