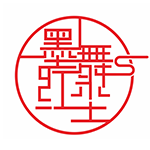工程队虽住在黄河边,只要连续两天不晒太阳,山顶没有融雪水流下来,工棚门外那口井从早到晚都滴不够民工煮饭的水。饭后洗了锅、添点水就着剩余的火温供大家洗漱,水面总漂着一圈油花。麦子问老赵:“饭菜里没见几滴油,怎么烧锅水反而油黢了的。”老赵拖着尾音,一脸无辜:“那啷个晓得呢。”无原因所在,无解决办法,好在其他人根本没反应,热水总是好过去河边洗冷水。
麦子从学校养成讲干净的习惯,一周总得洗一次被子,井里常常没水,她就把衣服被子拿黄河边去洗。河水清澈而宁静,阳光与河风甘甜温暖,远处的山岚还有积雪,日头下金光闪闪,时不时有水鸟飞过,若不想太远,这样的景色总是养人。何况远离了故乡也就少了故乡的牵绊,有一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轻松和从容。无风有月的夜,气温不太低的时候,男民工为了省出水给女人用,也结对去黄河边搓洗劳累一天的尘土。黄河边的夏日真是凉爽,在树荫房屋下坐一会儿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工地没有遮挡,太阳顶着人晒的时候,也有一串串火苗从毛孔里钻出来连成片。刚开始这群男人脱了上衣光膀子干活,不出半天就晒脱了皮,脱了外皮的肌肤像煮熟的牛肉。受到启发,老赵和麦子她们这群女的也学当地妇女用衬衣当头巾裹着脸干活,火辣辣的阳光被遮挡了,汽车跑过去的灰尘却遮不住,追着人碾,皮肤上、鼻腔里、库管里藏满了尘土和水泥灰。
麦子六月底去了一趟省城,去接老马从其他工地调来的大工,里面还有一个高考落榜生,名字叫广东,一个嘴角刚长出绒毛的男孩,跟来工地学技术。等火车的空隙,麦子乘机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家洗浴房花两元钱,洗了一个响亮的热水澡。身子刚落入喷着气雾和热水的蓬头下,身上跑出汩汩泥垢随水下落,在地上淌成一圈圈黑泥浆,换下的裤子,麦子拿回工地,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才软了下来。“你说,要多少水泥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麦子和粒儿讲起的时候,粒儿用眼神嗔怪道:“下次去我家洗吧,水,有的。”如果每个人都是粒儿该多好,麦子想起项目部的遭遇和一路月色,再次叹息。
麦子和贵祥叔都明白,今晚要账又无望了,决定返回工地。她推开项目部办公室钉在门框上那席厚厚的棉布门帘,天地一色清明,与室内濡湿压抑的氛围有前世今生的差别。“月亮真好啊!”她对自己说也是对紧跟在身后迈出一只脚的贵祥叔说。贵祥叔没理会麦子和好月亮,双腿好似被项目部一股无形力量拖住,又返身折回室内,给坐着的几个男人各打了一支烟。给那个微胖油腻的男人打烟时,贵祥叔明显委顿了一下,话语卑微得没了腰身:“马经理,真的要照顾一下,工地上没吃的了,开学工人要给娃儿寄学费,多少给点,万儿八千也可以,解个难!”
被称马经理的微胖男人眼皮都没抬一下,把头转去旁边对一个二十开岁,板寸头的男子,用当地话开口说道:“妈个*,解他妈个*难,谁给老子解。”透过布帘缝隙,傲慢侧漏到室外,像插入大地的一把刀柄,刀刃飞入天际插在了月亮的身上,麦子明显感觉到月亮疼得缩了缩身子。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不出十里就会生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可不管什么方言,唤妈的声音和那句脏话总是能一听就懂,融会贯通在庞大繁杂的语言体系里,仿佛启明星,只要它升起来必然会天亮,一出口就能懂得。麦子不想让贵祥叔知道她听见了马经理的傲慢,或许会让他难堪,径直走向院坝外。仍然堆着笑挨着把烟给屋里每个人都点上,贵祥叔才把身体从那间阴屋挪出来,又不甘地捞着门帘顿了一会儿,才下了很大决心地缩了手走向院坝,月光清扫着他走向大铁门的影子,把迅速归位的门帘和项目部重新推回死寂。
项目部所在的红柳村,恰好是这条改扩建公路的中部,上到山顶那个路段由老胡承包,下到县城这段贵祥叔承包。主要是为公路两边做浆砌边沟、堡坎和水渠,路面是另外一个工程队。项目部原来是一户养牛场,挂了项目部的牌子就有了项目部的威严。以前贵祥叔到项目部,经常被那个醉醺醺的看门人驱赶,贵祥叔拿过他一些烟酒后,老头只在面子上佯装驱赶。有了看门人的照应,白跑的次数少了。要不到钱还不是白跑!到底又不一样,怀着希望和绝望自有其不同滋味。
看门人还在值班室里摸索,麦子只好站在大门处打量夜色,进门靠左的院墙堆满了材料,材料旁安置着两台大型搅拌机,搅拌滴漏的水泥浆把泥地铺出一层又一层的灰白硬质,在月下像凝结的冰霜。搅拌机在月下依偎着入睡,像是白天吵吵嚷嚷说够了闹够了,温存一会儿。想来搅拌机也是可怜,一会吞一会吐的,也不管它们愿意不愿意,能在夜晚安静地陪伴着,也好。工地上那几对民工夫妻,干活时也是吵吵嚷嚷的,天一黑总是比那些单身民工早早爬进地铺。
说来和项目部的人也不是都没交道,他们来工地上放线,只要马经理不在,也和大家说说话开开玩笑。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还和麦子聊民歌“花儿”。马经理在的时候,这些人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二个马着脸,掉了钱包一样。马经理那辆越野每次来工地上也像喝醉了酒撒泼的醉鬼,稀里哗啦把一路尘土驱赶得鸡飞狗跳,还没从车里下来盛气凌人已提前降临工地。贵祥叔他们赶紧上前敬烟、汇报工程进展。马经理向来脖子高扬,嘴里装了一块自动马达,不停往外蹦跶脏话,每一句都向某个母亲致敬。
幸好马经理不会天天到工地来,只要他的车轮卷着灰尘冲来,那些做小工的女人嬉笑着模仿:“骂经理来了,贵老板嘛,又妈*的了。”她们叫贵祥叔贵老板,叫老马马老板。除了爱骂人的马经理,项目上管这段路的还有一个姓张的经理,几个星期来一次,到了工地斜吊眼睛走一圈,不骂人也不问进展。他的眼睛长得像小沈阳,遮阳帽帽檐向下,压在斜戴的墨镜上,不多不少晃完一圈,即走到下车的地方,挽着等在车外女人的手臂,旋即驱车离开,一去又是几个星期。
张经理来过几次以后,老赵把她的发现公布给大家:“快看,又换了个女人。”老赵还发现张经理的女人一次比一次丑,最近带来的那个女人没在远处等,和张经理一起在工地上来回溜达了两圈,身形比张经理粗壮高大,精致的化妆掩饰不了墨镜下大肉饼脸。与张经理熟悉的的王监理在他离开后掩着嘴给人讲:“这个女人比张经理大八岁。八岁呢!”说这个话的时候,王监理的手掌打着手枪一直晃,要是有子弹,估计对面那棵白杨树都成骷髅了。女人曾是一家医院领导,为张经理离婚,前面那几个女的,是在外头偷嘴的。有了王监理的补充,张经理仅有的神秘被稀释了。
老赵反应过来:“老女人不仅养张经理还给他养小的?”老王点点头:“妈个*,不是咋。”老赵放倒手里的铁锹,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坐了上去:“这些瓜婆娘,不晓得咋想的,有手有脚要去干这些莫名堂的事。”“她们肯定相互不晓得。”麦子不想老赵一直说下去,以前老赵是不出来的,这些年对老马反而不放心了,老马只要对工地上哪个女人好一点,老赵就会借机敲打。前几天来了一对老夫少妻,也没少多少,年龄相差十来岁,老赵说了几次那个女人家里有老公。女人干活踏实,不爱说话,很质朴的样子,老赵却总提防着,这话感觉就是说给那个新来的女人听的。
“这个女人怀疑老张了。”王监理看大家兴趣着,不舍得丢失存在感。“工地这么苦,又脏,不闻到“气气”哪个愿意来。”
“来晃一圈还不是回城了,老女人耳根软,张经理豁一下还不是好了,再说那些女人又没藏在工地。”老赵的话又杀去了路对面。
“昨晚住老那家的。”王监理强调。
王监理和贵祥叔他们租住在一户条件不错的村民家里,主人姓那,大家唤他老那,距离工棚有一公里多路。那家人有两个大炕,老那一家住去了偏房的炕。“那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睡一个炕?”麦子张大了嘴巴。“那有啥,喝点小酒倒头就睡了嘛。”

 【同题合奏】月下的麦田
【同题合奏】月下的麦田  送花(500)
送花(50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