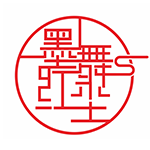小时候,母亲常会念叨一些记忆不全的戏词,逗我们玩。“……舅舅来了,杀公鸡,公鸡叫鸣呢,杀母鸡,母鸡下蛋呢,杀鸭子,鸭子飞到草垛上,下下了一窝小和尚。”这一段我们很爱听,但母亲并不常说。我们就自己说。在一些冷不丁想起的时候,傻乎乎的跳着喊着抢着比着说。母亲又气又笑看着我们闹,脸上现出佛一样慈爱深远的光。我当然不知道那时候的母亲,需要用一种博爱和禅境来对抗内心强劲来袭的凄惶。我也不知道这说词里的舅舅,怎么就如此大驾,能搞得人家家里鸡飞狗跳。我甚至不无认真的想过,那个人家家里还是蛮富的,比我们家强。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鸭子的样儿呢,母鸡倒是有一只,养它是为了能回收少量糟践掉的饭菜。公鸡就一定没有。因为买的时候,打鸣和下蛋只能挑一样,而偶尔能吃个蛋应该是民心所向。
那时候的我们一家,在一个地处偏僻气候恶劣的北方小镇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习惯性的过着没有一个亲戚半个老乡的双重意义的贫瘠生活。背井离乡和思乡之苦,是父母身体上布列着的奇异花斑。它会在一些特殊不特殊的日子里奇痒难捱,令人犯痴。这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涉足的古怪病症。在我们心智和思想的日渐完善里,也从不包括对父母身上那些无痕斑迹隐隐做痒的理解。因为我们从娘胎里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小镇接住的。而父亲当年万般无奈逃荒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小镇接收了他。
小镇和我们摩肩擦踵息息相关,但却不是我们的老家。也就是说我们的籍贯还另有其地。
我们知道父亲计划带我们回一趟“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那个年代,父亲微薄的工资,耍杂技般惊险的支撑着我们的六口之家。生活的沉重将思乡之心压的不得翻身。算盘珠儿怎么拨,回趟老家的等式都不能成立。那块思乡还乡之地,就一直在岁月的漫步中,无奈的撂荒着。而老家那边更穷。听父亲的意思,是连找到纸笔找到执笔的人再装了信封贴了邮票发出去一个简单的操作,都是为难。所以父亲写过去的本就为数不多的信件,因为极少有个回音只能以理解告终。而在我想象中,那些投放出去的稀薄的纸片儿,就好像是从灰茫天际飘去来兮的一片羽毛,让接到的人有着惶惑不真实的感觉。
这个特别糟糕的状况其实是父亲那边家里的一个写照。舅舅们这边还是能好点儿的。舅舅们家里会有黑白照片渐次寄来,附简短问侯。照片上的舅舅和由他们延展开来的家族成员全数可见,穿着认真并不着实寒酸,且个个眉眼精神。每有照片寄来,父母会对照夹在一个笔记本里的另外一些照片,指指点点的说,语气间好像有暖色的彩带轻柔舞动。我们总是兴致突来的凑到跟前,将空洞无邪的眼睛固定在小小相纸上,认真又马虎的认那些对我们来说陌生又古怪的脸。所以,舅舅在我,就是像标本一样被夹在书页里的照片。而这些“标本舅舅”们,在我心里站不稳当的清晰程度,模糊的丈量着我和舅舅们之间的汪洋苍茫。
父亲终于回老家了,但只带了姐姐一个人去。理由是姐姐记事了,可以认一下老家的模样。母亲也终于回老家了,但是带着弟弟和妹妹去。理由是弟妹小,带在身边放心些。我这个一直留守阵地的老二,总在用空白的方式汲取经验和填补缺憾。而在我这边,有一把糖果或者一本心仪的小人书为交换条件,未必不是一件窃喜的事。不去老家有什么大不了的?
父亲试图改观某种事实,尽量为老家做着什么。先后把老家的好几个堂哥接到家里来搞副业。舅舅则只有一个,那是五舅。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五舅不知因为什么心情愉快的梗着脖子转圈,忽然的就在院子里开始了高歌,把我们都下了一跳。那姿势和发音都太像公鸡在操练打鸣了。喉咙里纠结的声音一波高于一波的扯开,很算是填补了我们家向来不养公鸡的空白。我们那时很知道了顾脸,只觉得那样的放歌让邻院的小伙伴听见了,才是丢人。好在他很快结束了他的表演冲动。我带着感激,慷慨的记取了五舅这一值得眷念的时刻。
说起来,五舅在我家住的时间不短,而且那时我也很能记事了。但关于五舅的记忆,好像被剪辑磨损了一般,可以表述出来的就只剩这么一点点。
时光的手,一把摸下来,就揭去我们一层记忆的皮。
直到后来。
在和三舅的相处中,一种似远又近似近又远的东西触动了我,记忆才存留住了情节和感受的清晰纹路。
在我一路撂荒着的亲属观里,应该不大迷信有血缘就可以没有生疏。但事实是,我以二十岁不小的年龄和微有疏离感的个性,居然以小孩子的不觉自然的融入到了另外一个家庭。这在性格色彩深重的我真是全新的生命体验。
深夜被舅舅舅母接到的我,月色里跟着进了一个深深巷子里的院门。小小的院落被窗子里的灯光坚持的照着,并不昏暗。在一院子弥漫着月亮星星揉酿过的清沁的香气里,我看见花草茂盛的小花池,还有搭建齐整的小凉棚。这和自己数日来对家的念想,是一个很亲切的衔接。而缀着拼花门帘的平房,房间的结构摆设,和充满在屋内的生活底料的气味,无一不是从自己远方那个家里延展过来的似曾相识。小的表弟妹因为要加入的一个新成员产生兴奋,居然还没睡。他们不参杂质的脸单纯友好的向你贴近,这像一个柔软舒适的台阶,踩下去,脚面点触到踏实的部位。而舅舅舅母自然外露的淳朴亲切,以很享受的方式扑面我携带设防的嗅觉。庆幸满意中,我小心的排挤掉自己本能的顾虑,将自己疲惫的身体做成一个真空的皮囊,甩在他们为我准备的床铺上自由张合,沉沉睡去。
我五个舅舅中三舅是唯一在县城工作的。两个才上小学的孩子,谈不上什么负担。加上脱离了农事多年,活得算最体面。有些地方还可以稍作讲究。比如墙上非印刷品的四屏字画,比如玻璃柜里的大本影集。接下来就是我最熟悉的有关家族观念的场景了。大大小小的照片或桌子上或床上摊开来,大头小头对在一起,指点言辞间其乐无穷。我看到了一张令人吃惊的黑白照片。二十来岁的三舅在四川成都上大学时的留影。一张飒爽英气的脸,略带挑衅的眼神气质如外国影星,一点儿找不到农村孩子的影子。这张照片让我心里发生微震的地方在于,如此三舅怎么能和一个农村味儿很重的,看上去丑丑的且没什么文化的三舅母,有一场风平浪静的婚姻。
三舅安排两天的时间,带我去认了其他几个在乡里的舅舅。乡里被劳苦折磨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没有多大心思用在我这茬儿上。女人娃娃们负责招呼我。大碗结实的擀面顶着尖尖的鸡肉臊子端给我。我努力的咽下努力想记清一到五个数字的舅舅们容易混淆的脸。出于礼貌和不甘,我觉得我必须认下那些脸。但在饭菜少下去的时候,也是舅舅们的脸彻底混做一团无从打捞的时候。
很多年后,我努力规整这一段突出又浑浊的记忆,我做一个合理的假设。假设我就是出生在那些舅舅们身边,绊在他们脚下长大的一个“尕外甥儿"。那么我后来认为很重要的,有舅舅在身边的孩提,将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年轻时一定像土地一样蓬勃,但终于被生活拖累到顾不上敷衍我的舅舅们,是不是可以在我的成长中,皮实的撑亮一路温暖我内心的火焰?如果能,那将是怎样的方式和质地?然而,我每结构出一个看似稳固的框架,思维就紧跟出一个动摇它的缘由。而那些缘由的出处,如果追溯下去,就会在一个深暗的洞穴里无声熄灭。没有发生的故事,魅力仅在于它的幻化诡异,而不是满足你对真实的需求。舅舅们那些模糊的脸,嘲弄的设定了焊接事实的难度系数。而一个人的缺失,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一样,最终找不到恰位的补接。何况,我们谁也无法抽离掉,属于那个年代的资深的道理和烙印。
如果说一些空白的呈现,往往带着命定的硬度,无法抗衡,无法代换。那些被事实填补了的不空白的地方,就一定有状况要出来,表现为裂缝,或者粗糙的质感。我和我性情温和的三舅,就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出了状况。是因为三舅不断的在了解我。我的不参加高考,我的不努力工作,和我们能在二十年后相见的真实原因——我请了长假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出来晃,晃来晃去就晃到了他的面前。我像一个被聪明的人用眼睛挑开的一个烂草包,里面全是劣质的内容。这让生活态度严谨的三舅很不能接受。他忍不住用一个长辈的口吻克制的给了我训斥。我沮丧的接受某种事实。我知道这不光是代沟的问题。我一点儿没办法的是,我的日渐浮出水面并带着势气生长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这么冒失和不健康,有点儿畸形怪状且无法包藏。如果说时间空间地域习性带给我们的生疏,是可以改变的话,这些本就是人为意志的东西,再靠人的意志去转移那就难了。很知道自己无法符合和改变他的看法。我只但愿我一句话不说的样子别被他误会成倔强,我只是觉得申辩更糟才这样做的。性格色彩浓重的我,就这样悲剧而伟大的缄默着,做定一个不讨喜的小孩。直到舅舅送我到了车站,犹豫再三之后还是告诉了他,我按他的地址投了一篇稿子,有消息的话告诉我一声。

 【红尘有你】 一条河 陪着我们流
【红尘有你】 一条河 陪着我们流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