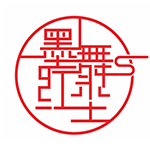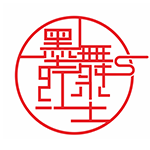街里人,下乡来,牛屎粑粑当锅盖。
那次,我气急了,违背了我不拾人家有用物品的良心。在村口一户猪圈里,赶开吃食的白猪,倒掉猪食,把一个敦实的铜盆藏在箩筐里。铜很值钱,卖废品也顶大人做几天工。很对不起那头白猪,它又要换一套餐具了。心里有鬼,几个月后我才再去哪里拾破烂,可发现它已经不要餐具了,猪圈里空荡荡。
在如今的同学会上,一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学,也谈起早年拾破烂的经历。其间的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同行,现在知道了也只有苦笑一声。他叫李永才,一个搬运工人的儿子。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看,他的出身非常可靠。的确,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资本,那就是穷。
我们都穷得没有童年。
然而,资本相同,同样不能比。他的穷是黎明前的黑暗,能够感觉到前面的光亮;我的穷却是走下沙市宝塔最下层的石阶,感觉黑得让人心悸。他能当兵,我不能,他能进国家单位,我不能。肖伯那次讲的道理,我读初中时就依稀明白了。那是暑假前,学校接到一桩勤工俭学的任务,给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重新上漆。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常年有部队守护。从来学校只有义务支农学工,这个假期能赚几十块钱,真是天上掉下馅饼。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报名了,兴致勃勃做好了接馅饼的准备。
最终没要我。
原因,你懂的。
我自然也懂了。连做个小工都不够格,今后能干什么?
然而,有人不懂,至少我们的班长就不懂。
班长叫郭淑清,是个南下干部的女儿。长相秀美,能歌善舞。她母亲很会持家,粗布衣裳,也能让女儿穿成公主的模样。我们读的初中是带帽初中,还是在弥市小学。弥小宣传队在全县有名,经常到县内各地演出,为小镇、为小学争得了很大的荣誉。而郭淑清是宣传队的第一台柱子,报幕、独唱、领舞样样都行,更有救场的急智。有人说过,宣传队可以没有带队老师,但不能没有她。她在舞台上出色表演,至今还让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咂咂称赞。我也同样记得,一次她在班上领唱《格桑花开满山红》,高音拖出来了,让人心发颤,那清亮的歌喉不遑让当今的歌星。有个叫王国平的同学,如今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班长,你是我们男同学的梦中情人。是之一。
当时他没说之二是谁,同学们散了后,他才告诉我,之二是另一个女生王运娥。她与郭淑清是不同的两类人,她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瓜子脸,天生带有一股吸引人的气质,按现在的话说是性感。那种骨子里散发出的妩媚,让人怦然心动。看见她,你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做的。这在当年不是好事,汹涌的革命浪潮,早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性、美丽和资产阶级一道冲进大海。感谢她们,因为有了她们,我们的童年记忆不再是单调的饥饿,也有了歌声和美好。
这是闲话,就此打住。
班长有特长,一辈子顺风顺水,在哪里工作,哪里都把她当宝贝护着。党把她的前途安排好了,一路上洒满阳光。她对我说过,你有才华,为什么不考大学?你没有努力争取,没有奋斗精神。
我只有苦笑。我能说父亲的历史问题淡化了,三哥的现实问题又来了?三哥廖国华造过反,文革一结束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报纸上电台上成篇累牍的高喊,杀气腾腾,坚决清除三种人!四类分子摘帽了,但在公权面前,又有了新的专政对象,危害政权的敌人,依然不断地被人为制造出来。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和他们的亲属,被所有的大学、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打上禁入标志。以前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遮羞布,这次干脆不用了。不取就不取,喊天也没用。
那时我正为恢复高考而激动,一次对我的文学老师黄大荣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几年文学理论。我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实力,可我没有这个命。我刚走出沙市文化馆的大门,就在六月灼热的中山路街头见到我家邻居鲁德英的弟弟鲁德品,他在弥市派出所工作,能提前知道一点江陵县处理三种人的内幕。他带来的不是春汛,而是彻骨的寒潮。我看着满街梭梭响着的葱绿梧桐叶,被烈日渐渐夺去水分,变得苍老起来,不由悲哀地想到,人的命运为什么总被不相干的事物所左右?
我不认为我没有奋斗精神,但我所有的奋斗都是竹篮打水。其实,现在社会上的情况可能更糟。那些励志的文章全是放屁,误导了十几亿中国人。比如,权威机构统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公司,平均生存年限只有四年。那些创业者不努力吗?他们没有奋斗吗?他们砸下所有的资金,他们投入所有的精力,难道只是争取一个倒闭?
这,只能用六个字总结:时也运也命也。
我承认,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艰苦的奋斗,才抵达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但别忘了绝大多数人连奋斗的资格也没有,而奋斗的资格绝大多数掌控于执政党的手中,并非人力可以改变。比如,五十年代教育部就规定,大学录取以工农出生和革干子弟优先。以后这种以革命为重、而不是以国家为重的用人标准越来越严酷,堵绝了无数有志青年的报国之路。别拿少数幸运者的事例来反驳我,那些骗人的榜样恐怕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相信。即使是真的,也是陨石砸到脑门心,地球人都不会中几个。
这是后话,与老街无关,担心写到后面没机会提及,故提前说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完全灰心。那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据说是周总理文革前在南开大学开座谈会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基础上。当时和现今的无数事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红五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它确实迷惑了很多人,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依然产生了寻找光明的动力。
初中时代,红卫兵过时了,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像班长一样的革干子弟成为第一批新鲜血液。随着一学期一学期过去,团组织日益壮大。在最后一学年里,连罗正喜也被吸收进去了。罗正喜的家庭情况和我相比,经济上优越,政治上相似。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医,由于是技术人员,在新政权下倒也无失业之忧,一直在弥市卫生院工作。罗伯不善言,但对我们说过一席话,我至今记得大概。他说他的外科本领是在战场上操练出来的,一台手术只用几分钟,该切胳膊就切胳膊,该砍大腿就砍大腿,容不得半分犹豫。不然,后面的伤员就可能来不及医治了。我听了倒抽一口凉气,人命真不值钱。
罗正喜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虽然因为出生关系,和我一样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但他像母狗子一样,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也有我、刘以德、陶永才这些人。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后,这些同学都不约而同到戏园子附近他的家里聚会。或天南海北神侃,或南街北街瞎转。刚建的虎渡河大桥,是我们指点方遒的平台。在虎渡河汩汩水流声中,我们坐在高高的桥头栏杆上,望着东北方夜空下荆州城和沙市的两团灯火,充满神往。回头再看弥市,几盏昏暗的街灯连行人的面孔也照不清楚。那时,大家恐怕都生出了逃离弥市、逃离闭塞的念头。
趁大家没有注意,罗正喜悄悄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我心里一咯噔,反问道,我够格吗?
他说,我够格你就够格,你写,我做你的介绍人。有一个团证在手,以后不论是下乡上调,还是继续读高中,都不会让人另眼相看。
虽然我对政治前途早就不抱希望,但为了今后有个安身立命的依托,我还是动心了,决定搏一搏。在他的热诚帮助下,管共青团和学生思想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
我很激动,以为组织上开始关心我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像骑车子上路,先要摸一摸前后轮胎有没有气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习惯。原谅我没提这个老师的姓名,事实上我也忘了他叫什么。那次谈话我受到屈辱,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他只是党的机器一部分。他的言行,是这部庞大机器运转时出现的正常状况。

 在老街成长
在老街成长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