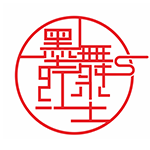大约一九九零年的一天,我婆家来了一个稀客,据说身份比较特别,一大群中老年妇女在堂屋里热情地围着她海吹神侃,从头到脚地评价她的穿着,满脸艳羡地夸赞她的品位,故作惊诧地感叹她的保养。我婆岿然坐在上首,以一个封建世家最高领导人的姿态面无表情地包容着面前这一群有失沉稳的晚辈。一个妇女用余光瞟了瞟我婆,跟着便问起贵客跟我婆谁更年长一些,贵客的具体年龄我已记不起了,但远没我婆大,大概也就比母亲长个五六岁的样子,总之不管怎样也是个介于花甲与古稀之间的老婆婆了。妇女们错愕地说,原来你比婆还小这么多啊,看起来她要比你还年轻哦。
贵客最先是在婆家露面,因而起初我以为她是婆家那边的亲戚,但后来她几次登门造访,都是住在我家,既没再往婆家去,也没别人围着她转了。母亲让我们叫她张孃,我们也没问起她跟我家的关系,但猜想肯定又是父亲在乡下认的亲戚。父亲与我不同,是个无论在哪里都能与人攀上亲的人:七十年代末火炮岩村一个跟鲁迅年龄相仿的老人是我大哥,九十年代一个名叫有钱的已经当爷爷了的中年人叫我大叔,还有一个让其他表兄弟们都摸不着头脑、不知从哪里凭空钻出来的大舅娘……
张孃一来,通常是母亲接待,两人各搬张椅子坐在檐下拉家常。来的次数多了,我们也慢慢知道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太太,丈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被枪决了,文革结束后,张孃在首都、省城和家乡等各地间多方奔走,要替丈夫平反,但她无儿无女,没人理会一个毫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因而平反的事始终无法落实。
有一次张孃又说到自己当年的光风霁月:在家有一群丫环服侍,出门有八抬大轿伺候,至于穿的绫罗绸缎、戴的珠宝首饰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母亲也在一旁附和,说她年轻时堪称一支花,皮肤那个白嫩哦,身段那个苗条哦。起初我跟大姐还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当说到她的长相之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互相做了个鬼脸,心中都暗自发笑:说她过去多么风光富贵也许不假,但说到美貌……就凭那不足一米五的个头、不合比例的长脸、黑得像酱的肤色、夹死苍蝇的褶子,多大的脑洞才能把她跟美女联想到一块去啊!
我不知道张孃到底有没有家,总之她来我家是太勤了一点,给人的感觉就是满世界不停地瞎跑,这家蹭一顿那家借一宿,没有个固定落脚点。也许她自己意识到了,说话处事就渐渐陪着三分小心和七分逢迎,我们家里每个人都被她赞了个遍。一九九四年左右,我遇到自初中一年级后就再没见过面的同学李大春,带他到家里来玩。或许是看到李大春掉了一颗门牙,张孃就夸我牙齿长得齐整,不像有些人这里缺一颗那里断一截,李大春大感愕然,我也非常尴尬,就把李大春带到楼上去了。
另有一次,大姐的儿子跟一个女孩在门外做游戏,张孃坐在门口看了一会,见母亲过来,就用闲聊的语气夸我外甥长得五官标致,面额饱满,一看就是福相,以后是要当大官的,然后又问这女孩是谁家的,母亲答是一个在隔壁我叔家租房的四川建筑工家的,张孃脸上立刻现出嫌恶。恰好这时女孩听见大人在说她,好奇地朝屋里看了看,张孃恶狠狠地吼道:“出去!”母亲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嘱咐她:“莫吓着人家娃娃。”
我也不知道张孃到底靠什么过活,一会说在做古董生意,一会说在倒卖文物,一会说是帮人介绍工作,一会又说是做家政服务。有一次她说她搞到了一种产自澳大利亚极其名贵的南洋养珠,最近手头紧,想便宜卖给母亲。说着从一个绣制得比较考究的荷包里掏出一团包裹着的手绢,层层揭开后露出几颗直径近寸、淡赭色半透明的珍珠,她在取珍珠时,还不忘从窗口向外东张西望一番,随后把窗户关上,窗帘也拉了下来。母亲瞟了一眼她手上的珠子,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这个是鱼肝油。”张孃愣了一下,干笑着把珠子重新包裹起来。
又一年冬天,张孃再次来到我们家。其时大姐打工回来,正在家里小住,一些同学朋友听说她回来了,便经常来串门,邀她出去跳舞或是聚会。有一个叫大陈莺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我家进进出出。张孃似乎很害怕她,每次见她来了,都会躲到后院去。大陈莺的美貌和时髦在庆祥县是出了名的,皮肤白皙泛光,身材高挑丰满,再加上爱穿中长的皮草大衣,站在比自己足足矮了一头的张孃面前,更加显得高不可攀。我知道人们面对在不同方面比如身高、相貌、力量、权势、财富、学问或是气焰等某一项上牢牢压过自己的人时,会不由自主产生出一种畏惧感,说话行事都会透露出底气不足的拘谨或畏缩来,然而张孃的反应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果然,当大陈莺走后,母亲便问张孃:“你那么怕她干什么?”张孃说:“她是工商局的干部。”
后来我跟大姐聊起张孃,虽然我们都没去打听过她的家庭情况、生活状态和经济来源,然而通过她的种种表现,我们都肯定地认为她是个走到哪里骗到哪里的江湖骗子。比如那次她用鱼肝油当成珍珠骗母亲,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火车上猜红蓝铅笔的、路旁押注猜骰子的、公交车上假装手机被偷,借人手机打电话,然后有人逃跑,借手机人去追的……庆祥县是专好出这种人的,无论城里乡下,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外地行骗,江湖术语叫做杀业务。这些骗子脑瓜机灵狡诈,手段五花八门,可都比张孃与时俱进得太多了。但在兜售“宝物”这一招数上,大抵离不开各种不测,造成不得不紧急抛售,因而把珍珠当成鱼眼卖的假象,利用人们贪便宜的心理,达到他们诈骗钱财的目的。
一九九六年是张孃来得最频繁的一段时期。她一来我家,还没进屋就大呼小叫道:“这回好了!这回好了!”我问她什么好了,她喘着粗气说:“儿子找着了。”我和母亲都很诧异,她不是一直没有儿女吗,这回又从哪里钻出个儿子来了?张孃喝了杯水,直到坐下来还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吼吼地说:“最近才打听到的,我儿子在张家界市水利局当局长,媳妇在妇联工作,孙子孙女都在上大学了。有钱得很啦,现在好了,有依靠了。”其时张家界旅游在全国范围才刚刚掀起热潮,叔叔所在单位上月就组团去过,即便是胜利街的农民们,也有不少人听说过这个新兴旅游城市,因而我们认为,张孃提出这个城市,绝不是脱口而出,而是有着精心谋划的,她不说北京上海,是因为这些地方知名度太高,显得信口雌黄,可信度不高,她也不说丽江平遥,因为这些地方尚不为外地人知,她说出这个才刚刚进入人们知觉范围,却又还没在脑海中形成固有印象的地方,人们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认同感:“哦,原来是那里呀。”
我们早看出她又在骗人,却不揭穿,还将信将疑地问她:“你原来不是说你儿子早死了吗?怎么又有个儿子了?”张孃说:“啊?我有说过吗?哦,我是说过,那时在打解放战争,我们被打败了,带着儿子逃命不方便,我就把他放在一家农户门口。我看那家房子破破烂烂,四壁透光的,有没有人住都不晓得。我也没抱希望,只想好人好运,菩萨保佑,万一就有人碰到了呢。解放后经过那么多运动,一直没有机会去找,等到六几年我找到那里,都没得人家了,我就以为他不在了,哪晓得人家是一个村全部搬迁了,他也跟他养父母离开了那里。阿弥陀佛,这个才叫老天有眼啊。”
我问她:“你去过你儿子家了吗?”她回答说:“还没去过,刚刚才得到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去呢。”我又问:“那他的家庭情况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张孃说,是某某帮她找到的,某某以前曾经帮她跑过平反的事,这回他去张家界出差,跟人说起她的事情,或许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的人里就有她儿子,就这样对上号了。
我一边听一边匿笑不止,其实关于张孃儿子的死,流传过好几个版本,但并不是他人以讹传讹传走了样,而都出自她自己之口,她毕竟年纪大了,自己说过的话都记不住,每次编完后就忘了,下一次再编出个新版本来,包括现在失而复得的过程,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又多出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呢?我问完后就走了出去,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借钱,这个场面很枯燥也很难堪,少一个人在场,借钱者就少臊一些皮。看她编得辛苦,也编得流畅,我就不去戳破她,反正后面的事有母亲来应对,我对母亲绝对信任,她吃过的盐肯定比我吃过的饭多,这种事情她是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的。

 张孃
张孃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