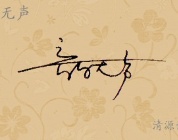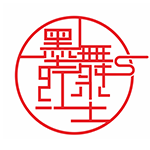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一】
我一路上的劳累都略过,进了家门,只是最简洁的问候和招呼,大家都没了心思关心其它。
叔叔带我来到她的床前,说:“阿妈,阿妹回来了。”
她缓缓转头向我。这时她的心智还是清醒的,眼定定的望着我,装着千言万语,嘴在动。我忍住进门就开始往外溢的泪,和叔叔都弯着腰倾身向前,极力想明白她的话,听到的却是单一的音节,类似“水”,再无其它。“水”艰难地重复着,清澈的眼珠一直定定的望着我,直到她也觉得这是一种徒劳,疲惫地转过头去,留余下的气大力地呼吸。
叔叔很平静,说:“舌头开始不听使唤了。”又说:“我去拿些糖水给她。”出去了。
他们都带着一张张隐忍着重重心事的脸进进出出,不多话,似乎很忙,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忙的,只是在等,等一个时刻的到来。我也只能如是。我站她的床前,听她重重的呼吸,心里忍不住轻唤:“奶奶,奶奶。”她的身子盖在被子里,一动也不动,只有对着我的侧脸配合着呼吸起伏着。叔叔喂她糖水,她不再张嘴,水顺着两边嘴角蜿延流下,我急忙双手努力去接,接不住,颓然缩手,心被抽了一鞭,一惊,手和心都空空的。
我只能静静的站一边看着她,和她之间隔了一层看不到触不着的让人心寒的东西,心悲凉地清楚着,她已决定不要我了。
叔叔出去了。我轻轻坐落她的床头,从被里抽出她的一只手,握着。我想得到一些温暖,却感觉了她的冰凉,然而柔软又如婴孩一般,她的手。手背大片瘀血,打点滴留下的,大滩的紫黑在蜡黄的底子里触目心寒,我心里一阵阵的紧,泪一滴滴的落。她却只是安静的重重地呼吸着。
我轻轻抚她的额,这个动作,我盼望了多年,起初是她的严厉,后来是我的羞涩,一直阻止着我。这是高贵威严的额头,满布岁月的沟壑,如今却充满无助。我触到一手的汗湿,以为她太热了,心里责怪叔叔们大意,脱去她的毛线帽子徒手去擦她头上的汗。那头稀少的灰白发,被帽子压成了枯草团。我的心又是一紧一痛,用手轻轻捋着那团枯草,心底的悲哀和依恋化水,一滴滴的落。她却睡得那么安稳,这世间所有的事都与她无关了,我也与她无关了。心底的茫茫然空落落一股没有方向的风一般,托着我轻飘飘的浮着。
她的额上还是有汗,也许真太热了,我努力的扶起她的上身,褪去她的一件毛线外套。记得过年时,坐在她的房间的矮凳上陪她说话。她平静地告诉我:“可能过不了今年了。”就像说别人的事,她的淡泊传给我错误的信息。我笑她:“这可不是你说的算,还长着呢。”这么精神的一个人,一餐吃两大碗饭,嚼肉的嘴依然有力,还能骂人,怎么会呢。我太年轻了,不谙世事,难怪总让她放心不下。一个多月前,婶婶就打电话给我,说奶奶想我回去。我一直拖着,不相信一个人会说走就走的。她天天盼着我回去说些话儿,可还是来不及了。脱了衣的她额上又开始凉,怕她冻着,我又给她把毛衣穿上,帽子戴上。
如果我能早回来两天,但世事没有如果。总是忙忙忙,以为她会等的。前年,她曾躺过一次医院,我也是拖拖拉拉的回来,陪她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叔叔也在电话里说可能不行了。但她多精神呀,能唠叨,说婶婶们的是非,多好呀,半夜要人起来切橙子给她吃,一会又吵着上厕所,整夜地叹息这疼那痛不让人睡。邻床的一妇人笑:“你奶奶像个小孩一样。”我也笑,告诉她照顾一个小孩真是又麻烦又劳累。可是那个时候,我烦得心里蹋实,能埋怨她,能取笑她。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了,她安静地躺着,把我独自扔在一个沉寂陌生的世界,茫茫然无所依。
房间里一片寂静。床前她的拖鞋摆得整齐;那只老锑桶里装有水,给她抹身子的,水早凉了;毛巾挂在床头,用得久褪色了,图案依然是我熟悉的;床头的方桌上,放着暖水壶和她的水杯,小矮凳上没有坐着人,人躺在床上了。灯影里,它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幽幽与我相望,无声诉着往事。
时间是零晨一点,他们都在客厅低头坐着。叔叔问我:“还要不要送医院?”医院就在街尾处。可她讨厌医院,曾哄着送去住,那时她还清醒,能自己回来,再不肯去。小婶婶与我耳语:“她是怕死在医院里。”我知道。于是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医生与叔叔说:“老熟了,尽心而己了。”她不配合,骂医生谋财害命,医生来两三次便不来了。都说她返老还童了,其实她的心比谁都清明,生老病死早己看得透澈。我答:“不用了,她想呆在家。”叔叔问我,是想表明自己尽了孝心,怕我责怪,我也知道,大家都尽心尽力了。
叔叔说:“应该不会走得这么快,你坐那么久的车,去休息一会。”
我和衣躺下,眼睛专注与木格子床架对望,格子里是一幕幕往事,慢慢走近,慢慢清晰。那一年,我五岁,被她塞进课堂和一群比我大得多的孩子排排坐,眼光光望着窗外的世界听老师唱天书。老师家访,交给她一本应写“人口手上中下”却画满了圆圈的本子。老师走后,她让我跪着,扬起一条一米多长的勒竹鞭子狠狠往我身上抽,我鬼哭狼嚎,却无人救得了,门被栅上了。然后一转眼,她就突然变得老太龙钟了。她整天晕沉沉地坐在门口一张藤椅里,看街上赶圩的人,如有人愿意陪她说话,她就来精神,告诉人家她有一个孙女儿,在外省很远的一个城里,跟人说这个孙女的点点滴滴。她常常突然拉着别人的手问:“你是阿妹吗?”“不是,阿妹哪里有空常回来。”她便歉意地笑:“人老了,眼花了。”在她寂寞的岁月里,我是一个狠心的不孝子。
夜很安静,楼下厅里的大吊钟传来清脆的一声响,一点半?还是两点半了?
【二】
“你们快起来,看样子准备不行了。”二叔在楼下喊。
二叔站楼梯口仰着头向二楼睡觉的人催促,见我,说:“准备不行了,开始出口水波了。”
他们为她在客厅铺一个地铺,用早准备好的旧门板。两个婶婶到处翻找挂蚊帐的绳子和细竹,急,有些乱,一个不小心踢倒了凳子赶紧扶起,没有唠骚了。
她重重地呼吸着,如我上楼前一样,只是半张的嘴聚着一团怪诞的口水泡,随着呼吸轻微颤动。我站在她的床前,不知所措,感觉这个正在作垂死挣扎的老妇人很陌生。我徒劳伸手在她睁着的眼睛上方来回晃,盯着她的眼珠,盼望它们能随我的手势转动,我甚至想伸手去抹那怪诞的口水泡。小时候她要出远门不便带上我,我总是又哭又闹,死拉住她的衣袖,或抱着她的小腿不放,被她硬生生的扯开甚至拿鞭子赶,还一屁股坐地上一手鼻涕一手泪的抹着哭着,一直到她消失在路的尽头乃不尽意。现在我眼睁睁看着她越走越远,只是痴呆,死神来领她走了,神秘、敬畏、愕然却把我变成了一根木头。
叔叔抱她出客厅。她软绵绵的任由他们摆布,胸前的那口气弱下去了,身子都似被剔去了骨头,让人不忍看。
有些乱,叔叔迷糊,挂蚊帐几次都掉下来。婶婶不敢进她的房间,叫我去拿几套新衣给她换上。哪来的新衣?婶婶说:“她留着,买给她的不肯穿,你奶奶早有准备。”
与她的淡定从容相比,不习惯死亡的是我们。
为了给她找换的衣裳,我打开她那只笨重的木箱子。她一向不喜明艳的色调,衣服不是灰黑就是深蓝,我一眼就看到我读中学时穿的校服,镶着白边的藏青料子,夹在她的灰黑衣裳间。几年前一个春天,我回来探亲,有几天倒春寒,我向弟媳借厚衣,她说:“你有衣服在家,不用借。”大家惊讶地注视着她递给我这套校服。那次大家嘲笑她,我以为她丢了它们,却还在,后来我有意留给她一件如今穿的灯心绒冬裙,暗示她我长大了,它们都被叠得整齐放在箱底,被压成了一份沉重的思念和一段冷寂的岁月,猝不及防地与它们相遇,似被狠抽了一巴掌,我的眼睛和喉咙一瞬间辣辣的难忍。

 送奶奶
送奶奶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