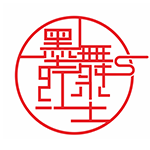我们家很早就为母亲的后事做准备了。
母亲从我记事起就多病,就是农村妇女常见的那种心口病。所谓心口病,其实就是胃痛。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比母亲轻得多,时好时坏,竟也伴随我二十多年了。我常想,母子同得一种病,幸也?不幸?或者说,上苍是怕我忘了母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
多年来,母亲的胃痛常常在晚上或大半夜发作。白天好好的,照常上地劳作,跟好人没甚两样。也可能是母亲不愿说出来,强忍着,怕误了农活,被人笑话。我老觉奇怪,都胃痛了一晚的母亲,怎么白天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直到现在,村上的人一提起母亲,还是赞不绝口:小奶奶(母亲辈分高,村上的大人娃娃都习惯了这么称呼)别看人瘦得跟麻杆子一样,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比哪个人慢。
有好多次,母亲在说到她过去时,总要提及她曾在公社受过的表彰:说因为她劳动突出,除被公社在大会上表扬外,还奖给了她一把尖头铁锨。那把铁锨,五年前不知怎么被姐姐从杂货屋里又找了出来,之后如获珍宝地拿回她家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母亲作为一个农妇一生当中所获的最高荣誉了。怪不得母亲每次说及时,仿佛一下子又来了精神,看得出,母亲对这个荣誉无比自豪。
母亲胃痛起来很骇人,常不住地呕吐,有几次竟差点昏了过去。从小到大,母亲出现这种情况我都说不清有多少次了。不但母亲,就连全村的人都认为母亲去是迟早的事了。据母亲讲,有一次,她病重得厉害,甚至地区医院的大夫都没有一点办法了,他们劝父亲应早作准备。一向坚强的父亲,当大夫当面这样告诉他时,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而被病折磨了那么多年的母亲,可能对自己的去已看的不是很重要了,唯一让母亲放不下或牵扯的是,她怕某一天她去了后,我们都成了村上那几个没娘娃的样子,这才是她心痛或难以割舍的地方。
村上当时有一位老中医,正是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母亲的病竟奇迹般地有所好转。尽管那位老中医都去世多年了,但母亲多次都不由自主地念及他的好,说:“若不是大老(村上对那位老中医的敬称),我早没人了。”母亲所说的大老,我一直还有印象:高个,给人就诊时常坐在炕上,前面放一炕桌,炕桌上还有一号脉用的脉枕,因看病时间长的缘故,那原本红颜色的脉枕已变成黑红了。
父亲更是对这位老中医推崇备至,每次提及时,都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大老,城东乡谁不知道,上兰州医学院的时候,人虽丢盹(打瞌睡),但老师讲了什么他全知道。我常想,一个人在他去世的好多年里仍能被人引以为豪,不能不说是做人的成功。一个村庄里要出这样的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呢?也可能是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或十几辈子。
好多次,父亲曾和母亲开玩笑道:“若某一天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要走的话,你肯定在我的前面。”父亲一生身体硬朗,即使七十多了还犁地干活;而母亲呢,一辈子都病病恹恹的。可能父亲是这样想的,有他在,即使母亲走了,他也能把母亲的后事料理得圆圆满满的,也算是对母亲陪了他多半辈子的一个交代。可谁知,父亲却早早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许多时候,无常让谁先去,让谁后去,一点都由不得人自己,或者说,许多时候都是出人意料的。
父亲病重的时候,亲眼看着让木匠做了两副棺木,其中一副是给母亲的以后准备的。早在很多年前,父亲就意识到了人迟早有这一天,就央人从南山里早早买来了松木,做完这些时,他感觉了了一桩迟早要面对的大事。也许,父亲对母亲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父亲对母亲的好,不仅在生前,即使在他弥留之际,他都深深惦着母亲及母亲的后事,想尽力能为母亲多操心点什么。
父亲去了后,母亲的棺木就静静地放在杂货屋里。每次看到它,都让人想到死亡是如此的近而真实。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母亲以及姐姐们都共同为她的后事默默地做准备了。
有次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从来不照相的母亲,竟主动提出也要照一张,并说万一哪天她走了,可能用的上,免得急用时让娃娃们手忙脚乱的。在照相前,母亲特意换上了她平时只有走亲戚家或进城才穿的衣服,并在头发上沾了水,而后用梳子细细梳好后才出了门。
对于老了后的那天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母亲一直老拿捏不定。颜色太艳吧,对劳动了一辈子的母亲来说,老感觉与她多年的穿着习惯不相适;太俗吧,又觉得怕被人笑话。每次,听说村里谁谁的老衣已备好了,母亲总要前去参考参考,以便自己好下定决心。我老想不清,平日里总不很讲究的母亲,为什么对她老去时的穿着却那么上心、在意。
有好几次,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母亲总要把几年前就备好的老衣从箱子里拿出来,一边穿,一边让我看合不合适。我发现,平日里一直俭素惯了的母亲,穿上新衣后,竟有点不自然的感觉。想到母亲某一天将穿着它到另一个地方去,我的泪竟不自禁地留了下来。母亲见我这样,便默然地将衣服叠好后放在了箱底,可能是母亲由此也感觉到了我对她的不舍吧。
从小时到如今,我真说不清村庄上有多少人走了。我老觉无常就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冷漠地一个个地点着我们村庄上的人的名字。有时七八年八九年点一个,有时两三年点一个,更有时一年点好几个。它点人时,大多从年长体弱者者依次开始,有时也不,也可能是它看错了,把我们认为最不应该去的一个人点了一下,比如说我哥,我外甥。母亲老认为无常即使点时,按理点到的应该是她,并且母亲也愿意是她。可是,他们却早早地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这是母亲最不愿接受和痛心的事,但,谁也拿无常没有办法。
我记得我哥去世时,母亲一边用头撞着地,一边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嚎哭:“老天爷啊,你怎么不长眼睛啊,你怎么不让我代替我儿子去走啊!?”平时柔弱的母亲,此刻竟好几个人都扶不起来。还有,当母亲听到远在异地读书的外孙不幸夭折的噩耗时,母亲竟不停地用力左右扇着自己嘴巴,人劝也劝不住!一辈子从未打骂过子女一下的母亲,竟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指责:黑头子都走了,我白头子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啊!
在一年年中,我村庄的好多人都相继走了: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老大夫走了,在村上当了几十年队长的老胡走了,缠了几十年脚见人总笑嘻嘻的老邻居走了,年纪轻轻就撇下子女不知该称小孟还是老孟的他也走了……我怕某天母亲也随了他们去,尽管我多么地不愿意和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把母亲藏在某个无常发现不了和忘记了的地方,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
晚年的母亲,每天都专注地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早晚的念佛。不管阴晴,从未间断过。母亲没上过什么学,念佛时,仅会念“阿弥陀佛弥陀佛”那一句,由于再没有记下其他的,母亲就把那一句反复地念。念完后,因惦着庄稼,母亲便到庄前庄后的地里转。我想,那一茬茬的庄稼们可能都记住了年老的母亲每天走路的姿态、对它们的依恋以及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抹泪的情形,只是它们没说出来而已。
如果说把离去看成是人生的另一场旅行的话,一生都病病痛痛的母亲,可能在很多年前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多年的日子里,母亲到底为此做了多少准备与不舍,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再往下细想。
母亲走的前一天,是正月十六。那天,我陪母亲走了很远,先坐车去了南城门广场,后又陪母亲去了大什字广场。不知怎的,我那天有种很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和母亲合一张影,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但转而又想,天气还有点冷,等转暖了和母亲再照也不迟。现在一想起,我都后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可能是我此生中唯一不能弥补的遗憾了。

 母亲的后事
母亲的后事  送花(12)
送花(12)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