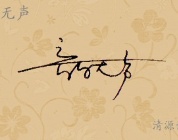飞渡那荒凉依旧的春季草场,一缕春水悄悄萌动,银白色的情人河依旧那么狭小。而长风却先声夺人的呼啸而过,无垠的草海起伏不停着金色的波浪。长风吹低黄草,隐现着挤在一处静卧的牛羊。长风撕扯牧人的衣裳,让他们衣裾在风中厚重的飘扬。低着头,握着套马杆,或向着天边独自怅望,却没有一个人会在风中歌唱。猎猎的长风吞没了歌声,却将他们的衣裾摇曳如旗,共同幻化进这一片野茫茫、天苍苍。
天地昏暗,白发的额吉在毡包里诵经。当寒流与祈祷同在,我只想像初生的牛犊一样挤进你的毡房,同那明净如婴的眼睛一起,注视着你那如豆的昏暗灯光。西面的天空云锦灿烂,热情如火的贲张燃烧。一天纯净而艳丽的霞光,羊群在金黄的草地里穿行,一路扬着膻腥的灰尘,金黄色的草屑随风飘扬。我注视着那面容阴郁的牧羊少年,他一直低着头,怀里揣着一只新生的小羊。他的羊群像潮水一样汹涌在我家的木栅栏外,金尘袭天中,一群羊边走边啃我们挂在栅栏上的干白菜,记忆中的我一直在向他奔跑,奔跑着渴望与他同在,而他的身影却一直那么遥远。只是轻轻地挥着鞭子,拢了拢羊群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遥远的南部的村庄,在金色烟尘的笼罩下迷离如梦,渐行渐远的灰暗羊群刻画着你的不散忧伤,你让我心痛到如今,那忧郁无言的牧羊少年。
这些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未免让人过于神伤,枯黄的草色飘舞如沙,春天的脚步分外蹒跚。那八百里波澜壮阔的金色瀚海,我只想为你歌唱。
尽管,我是如此渺小。
夜半静的出奇,我倍感孤独,所以我想起了你――那不言不语的白发额吉。返青的草场,微风拂过时让人陶醉,情人河的一带清流正涌动着细碎的冰凌。你在河畔汲水煮茶,你的男人在草地边缘粗放地耕种。解冻的黑土酥润如酪,他不成腔调的歌声悠然飘过。
谁也不知道额吉一家什么时候来到这里?让桔红色的土岭下多了一座黑色的泥屋。直到黑泥里夹着的黄草,干脆苍白,房顶上已青草离离;直到他们悄然老去,两个女儿都嫁作人妇,这个问题还是无人知晓。夏天的草地丰美而平静,它是那样宽容,坦诚地接纳随时来到这里人,不管你是落魄流浪、放牧畜群、开垦种植还是在平坦舒展的坡地上插木为篱,堆泥成屋。
那一坡不知是谁种下的向日葵,已破土成苗。在明媚的阳光中静静结蕾,碧绿的花盘紧锁着娇黄的花瓣,摇曳,亭亭如二八之女。生机勃勃的绿草像光滑的锦缎,点缀着一地花朵。牛羊的毛色渐渐发亮,小羊和新种的作物一起成长,这是草原上最美的初夏时光,它在众多美丽的民歌里永恒传唱。
但是,明媚的初夏太短暂了,阳光一下子就变得炽灼和狂野,连空气都倍加透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催促牧草长高、玉米成熟,让一坡坡娇黄玲珑的向日葵,一改往日形状,金黄绽放、仰首视日、艳丽张狂,狂热得像马背上不羁歌唱的悍妇。强烈的日光把白杨由嫩绿烤成深碧,深绿色的卫士般沙沙护卫着桔红色山岭下的安宁一隅。天空蓝得让人大彻大悟,向日葵像金色的火焰点燃了一面面缓坡,明亮炫目的彩色和坦荡热烈的芬芳,让人沉醉让人警醒,让人顿悟于生命的热烈与赤诚。
正是在这备受礼赞炽热骄阳下,额吉的男人――韩叔(全村人不管老少都这样叫他)牵来了一匹神采飞扬的枣红马。他肮脏褴褛的衣衫里飘着隔夜的酒气,浑噩而猥琐,但他像从日光中走来,须发之间金光流溢。那匹十分骨感的马长鬃如火,在金色的阳光中红艳的猎猎抖动,它用蹄子刨地、它轻声嘶鸣中带出一股刚猛的气质,深栗色的大眼睛那样明亮那样透彻,让众人赞叹;韩叔笑得那样得意而张狂。在他们身后是一幅壮美绝伦的图景,远远的水泽被蔚蓝的长空笼罩,流云飘渺下,水气蒸腾的碧绿草地上数不清的骏马在腾跃和长啸,它们高举双蹄竖直成飞翔般的神态,仰首长啸时长鬃飘逸,这生生不息的力与美的渲泻,被定义成为了草原的图腾。
在这样一幅喧腾的图景前每一位骑手都会热血贲张,那仿佛还沉浸在昨日醉梦的韩叔竟轻灵一跃,跳上了马背,额吉挽着念珠,急切得向前走了几步,她厚重的裙角扫过满地的马兰花沙沙作声。松松跨跨地高坐在马背上的韩叔已抡起鞭子击打马股,那红马的肌肉紧张地颤栗了一下,便像风一样的开始狂跑,人群开始了惊异张望,因为韩叔御风而行的快乐实在太短暂了,不堪的骑手和毫无理由的击打触怒了神俊的红马,它跳腾转侧,高举前蹄怒气冲冲的一声长啸,仅这一下,韩叔就从马背上重重跌落,跌落在露水丰莹的夏季草场上,砰然有声让人心惊。
额吉挽着念珠匆匆赶来,韩叔躺在草丛里一动不动,我想起刚才那红马长鬃飞扬的样子,它举着碗大的蹄子,在金色的逆光中矗立成雕像,韩叔就在它的蹄下,它萧萧嘶鸣着轻轻落蹄,把蹄子落在远离他的地方。
“真是匹仁义的马呀”人们议论着围了上来,额吉关切的望着地上的男人慢慢地坐了起来,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半身没在碧绿的长草中,痴呆呆的好像还在作梦。“他没事――”人群里发出了善意的轰笑,韩叔站起来了,他抖落了一身断草,青草的芬芳让他清醒,接下来的事,让善良的牧民不耻,清醒过来的韩叔一把拉紧马缰开始用鞭子拼命抽打枣红马,马垂着头,静静的忍着,近乎疯狂韩叔鞭如雨点,红马垂着长长的睫毛,我感觉到它清亮的大眼睛里盛满痛苦。
人们默默的散了,没有人理会这种不体面的冲动。
而后不久,红马不见了,韩叔也不见了,有人说红马是军马,韩叔犯法了。
额吉一言不发。
那一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男人帮助的额吉独自收拾好羊圈,而后她就那样呆呆的立在雨里,暴雨倾泻如注,天色蓦然黯淡,不辨昏昼。细细的情人河盛不下这么多水,疯了似的泛长数倍,夹泥带沙一路奔腾,我看不清额吉是不是在哭,她的脸上雨水横流,暴雨冲涮过的草原,将初洗如婴。
韩叔再回来时夏天已经结束了,他迈着醉汉特有的步伐回到额吉的小泥屋,金色的秋风正在将东部的草场渐渐染黄。一群群候鸟就要踏上南归的征程。
这时我才发现在那收获不尽的金黄色牧草深处还有这样一片美丽的湿地。金黄的草地向天边消长,与湛蓝的天空远远相接,而那一湾水泽,就这样静静的铺展在那里,闪着金光。秋天的草金黄而充满韧性,它们在风中漫漫飘摆的样子就像一场舒缓而优美的舞蹈。岸边矗立着几头悠闲的牛,静静的嚼着短短的草,水泽的周围污黑泥泞的一片,被牛羊踩踏的十分松软,水面就静卧其中,不是湛蓝,不是碧绿、不是洁白,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它是透明的,折射着日光,剔透无比的呈献着黑土地的颜色,让蓝天和白云倒映在里面也顿时失色,像是叠加进那透着黑土色的水中,静静的凝滞不动,任凭金色的阳光闪烁跳跃,幻化成分外神奇景像。
水泽的那一端有人撒网捕鱼,银闪闪的网落进水中,呼啦啦的惊起一滩鸥鹭,那些美丽的鸟儿,拍打着银亮亮的翅膀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而那深深的静静的苇丛,安宁甜蜜有如闺阁。就是这一湾静卧在黑色泥沼中的金光闪闪的水,让草原有了生机与活力,它静静的滋养着草原,以一丝母性的温柔茵蕴着这广阔的土地。“乌云,你在干什么――”韩叔不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他赶着一架吱吱作响的木头车,车上散乱着一些蘑菇。那些棕色的蘑菇,个头都不小,虽然早过了采蘑菇的季节了,但这蘑菇还都很漂亮,鲜美丰盈。韩叔身上散发着朽木的味道,穿着一双长统雨靴,他和马都湿淋淋的,韩叔说今年雨水大,林子里积了很厚的水。这时有一只白鹤掠过水面,像一道银色的光芒乍现后远去,只有圈圈涟漪在水面上飘荡。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